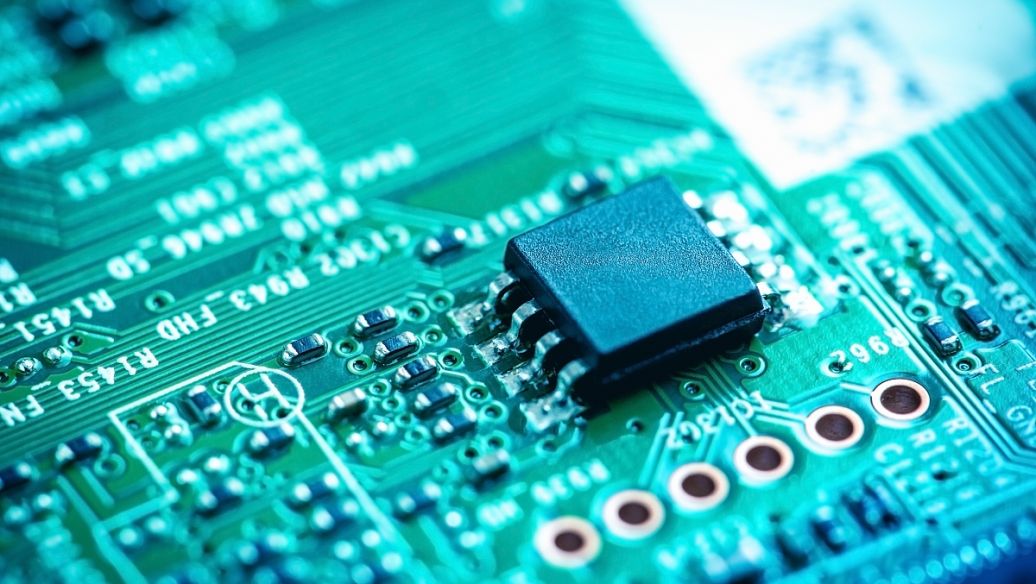「……君、松田君!」
少女的呼唤将罪木跌入回忆的思绪一下扯回现实,她面朝少女疑惑地眨眨眼,目光沿着少女指尖所向的位置探去……
探,去。
——咦?
油然而成的惊悚仿若一只冰凉的手拂过颈脖,脸颊上涌来一阵什么东西一滑而下的粘稠感,一秒后罪木惊觉那是她自己的冷汗。她逐渐放大的瞳孔映出淋满鲜血的模糊肉块,鲜艳地在她的视网膜与记忆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随之带来的痛楚令罪木猛然意识到这是确确实实的现实,于是她握紧少女的手又松开,只身走近血肉模糊得无法辨识身份的尸体,装作若无其事地开始检尸。
烂成血红一滩的肉块令手无任何器材的罪木无从下手,很快她就从红得刺眼的色块上撇开视线,试图用寒冷刺骨的手贴上脸颊,令混乱如麻的大脑暂且中止运转。还未整理好思考回路,一直一言不发地旁观的少女蓦然道出的话语,将罪木的思绪多少拉回了现实一些。
「想要知道那个人的死法?」
「诶诶?啊,是、是的……」对疑问给予有些支离破碎的肯定,罪木偏头困惑地向少女投去一瞥,随即擅自将这贸然提问理解为少女对眼前惨状的恐惧,罪木一面吐出安慰字眼,一面试图用冷汗密布的手去温暖少女本该丧失温度的脸颊——然而却在触碰对方肌肤的刹那,猛地发觉对方的体温比自己正常得多。一瞬被舒适温存晃了神智,罪木怔了半响才想起满怀歉意地低头认罪,准备收回的手却被少女一把握紧,随后又轻柔松开。少女迎着罪木不解与歉意交织混杂的尴尬目光,给罪木留下一抹意义不明的浅笑,迈开步伐来到尸体附近。
「实际上这个人,是后脑砸到钝器殴打而死的呢,至于为何会变得这样血肉模糊……」
少女紧盯尸体突然道出的死因判定,成功地给罪木混乱不已的脑内再蒙上一层迷雾,不知如何是好,罪木只好随口附和着少女的说辞,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向尸体上那疑似后脑勺的残块。未等她观察仔细,少女陡然抬起的脚又令罪木无暇理会其他——缓缓地、缓缓地抬高的脚,向其下的血块狠狠落下。
「那是因为……在晕厥后被如此反复折磨过啊!」
踩下。践踏。扭转。
飞溅的血液为少女满溢愉悦的腔调添上几分毛骨悚然,本就残缺不堪的肢体在重击下逐渐剥削出森白骨头,冷冷反射着梦境一般的可怖现实。从少女不断落下的双腿中瞥见浓浓绝望,即使绞尽脑汁也思考不出前因后果的罪木被无助茫然束缚原地,任凭飞越半空的血液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雨点般倾注而下,在她的身体上留下几抹粘稠,噼噼啪啪地奏响相比真正的雨水更为沉重的闷响。
依旧呆然伫立,罪木中止运转的大脑总算有了些重启的动静,她觉得自己应该去阻止少女,但哽在喉间的字眼无论如何都难以拼凑成完整句子,于是她拼命咬住下唇,凭借痛楚从迷茫手中夺回了身体的主控权。罪木惊慌失措地跑去想要为少女不明所以的疯狂打上休止符,而少女却在罪木靠近的前一秒将已然辨认不出人形的物质抛于脑后,蓦地回首扑进罪木怀里。
温热吐息拂过耳垂,罪木随之一抖,紧跟而来的是少女的轻声细语。
「呐,你一定会包庇我的吧?」
「——『松田君』。」
出其不意的三个字瞬间使罪木从混乱中惊醒,然后,再次坠入另一个用虚言编织而成的飘渺梦境。她将头没入少女被血液浸湿的长发,柔声给予后者肯定答复,同时幅度不大地轻轻颔首。少女满足了似的弯起眼眸,随即如断线人偶般颓然瘫下,使得罪木一个重心不稳险些连同少女一起摔倒在地。罪木晃晃悠悠地扶起再度褪去所有色彩的空白少女,脑内重现着与少女的初会之时。
「果然,就算失去记忆……」双肩轻微颤抖,罪木露出与残酷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明媚笑颜,在她始终未变的亲爱绝望的额间落下一吻。「也永远会是『绝望』呢。」
撤下笑容时,不知所措这一词汇已经彻底从字典中消失,罪木尽可能地淡去附着在身体上的血迹痕迹,然后伸手遮掩少女仍未睁开的眼。正当罪木准备离开时,少女却不应时节地赫然苏醒,眼部泛上的冰凉使她打了个冷颤。罪木的手掌成功地将不成人型的血块抹消在进入少女眼膜前,可是指缝中隐隐透出的鲜红却令似乎她明白了什么,恐惧通过瑟瑟发抖的身躯传递给罪木,而罪木边阻挡少女的视野,边扶掖着少女迅速逃离现场。
好在这里离病房并无多远,碰见人的几率也相当小,令罪木得以顺利回房。
将少女轻置在床上,再三检查门锁确实锁好后,罪木心安地长呼了口气,回眸望向少女,后者的瞳孔此刻已爬满恐惧、迷茫与迷惑,无论哪样都是罪木这段时间再熟悉不过的情绪,所以她惯性地用笑容来传递「别害怕,你看,我是『松田君』哦」诸如此类的虚言,以平复少女高鸣不已的心脏。
大脑溺毙在铺天盖地的谎言中,少女逐渐平静下来,露出了一如既往的笑容,随口抛出几个话题自娱自乐起来——就这样迅速取回日常,并对先前所目睹的一切只字不提。虽然也有恐惧与不愿混杂其中,但驱使少女这么做的根本思想所谓的「因为与我无关所以怎样都无所谓」,即使这件事真的与她有不可磨灭的关联,反正已经在记忆里泯灭得无影无踪,也不会遭到、不可能遭到任何人的谴责。
因为唯一能够谴责她的罪木将她视为一切,而她也将披着『松田君』皮囊的罪木视为一切。除了对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过过眼云烟,都是无所谓的东西,也无关希望亦或绝望,这只是纯粹的爱罢了。
完美的爱情关系不是吗?
至少罪木对此持有肯定答复。
只要小心翼翼地守护用谎言编织而成的虚假面具不被瓦解,将少女某种所映出的光景改写成名为虚假的真实,她们就可以一直在这层充斥虚言的膜中二人独处了吧。无论被谁指责,无论被谁怒骂,无论被谁冷嘲热讽,只要隔着这层膜淡然注视直到他们离开便好。不受分毫外界影响,感受彼此的存在,在光也传递不到的黯淡中把对方溢满爱意的瞳孔扭曲成除了对方容不下其他任何的玻璃珠。如果罪木的预想正确,或许她还能够亲眼见证黑羽蝶的破茧而出,在世界上空肆意挥洒着染名为绝望的剧毒鳞粉。
「所以。」明明先前没有对话,罪木的连接词却使用得理所当然。「在那天到来之前,『松田君』一定会永远守护你的。」
——请原谅,我这如此虚伪的虚言症患者吧。
对那在余晖下熠熠生辉的耀眼细粉满怀期待,罪木为包围着她们的膜再度播下了事后无法挽回的弥天大谎。
——气泡般脆弱的谎言之膜仍未破损,那是因为,膜的外部还环绕着一层更大的谎言。
——那么,又是谁诈骗着谁的虚言?
非常地非常地非常地非常地非常地非常地非常地不愉快。
所以为了发泄压抑在胸口的不满,她狠狠践踏着脚下的尸体,不知早已断气还是丧失失声痛哭的气力,除了血肉狠击大理石的闷响,什么尖叫亦或哭喊都没有传入她的耳膜。然而这却令她的不愉快指数随之高升,她砸了咂舌,射门似的一脚将尸体踢出去老远,在与墙壁亲密拥抱完后僵硬地摔落在地上,眼球从凹凸不平的脸上滚落。
她俯身拾起,粘稠感随即缠绕上她的指尖,手下意识地开始施力,眼球在她手中逐渐扭曲,在似乎要爆裂的前一刻由于过于粘滑而忽然掉下,躺在鲜红中任由灯光将它装点得仿若塑料模型。她瞥了眼那颗眼球,没有再度理会,右腿却不安分地朝尸体的难以辨认是哪一人体部位的某处踢去,早已被血着染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布料与她的鞋子摩擦发出鞭打般的声响,晃晃悠悠地拍打着墙壁。
好似全然不怕这响声会引来其他人——那是当然,因为那样也别有一番绝望风趣。
但是令人绝望的是她极其清楚这个时段绝不会有人经过此处,这是动用她超高校级的才能分析得出的结果。在这之后还有更值得一看的好戏,何必先在这种微不足道的绝望上一败涂地?
最后一击将尸体的脑袋与脖子调整为完美的直角,她轻笑一声迅速离开,谨慎地观察没有留下足迹后,她满足地闭合房门,走进浴室开始处理满是血垢的衣物。黯淡月光给宁静病房蒙上许些梦幻,仿佛方才的一切都是幻觉似的。但挥之不去的粘稠触感仍在指尖隐隐作痛,她抬头眺望即将破晓的天空,然后爬上床闭眼稍作小憩。
医生如往常一样准时到来,她压抑住内心的喧闹,在尽心尽力地掩饰了一段时间后,迫不及待地背对医生握住冰冷门把,知道对方不可能拒绝自己的请求,她微笑着走出门外,故意用亲热举动麻痹医生的思考,借散步之名成功地将医生引到现场。
那么,序幕的帷幕就此拉起。
「呐,其实我根本没有丧失记忆。」
心怀讥讽地观察身旁那个明是医生,却也是患者的人满是期待的神情蓦地惨白一片,她将讽刺藏于背面,大笑了起来。
「啊哈哈哈哈哈,骗你的啦,看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开个玩笑罢了。」
「真的,是骗你的。」
为了否定前言而特意加上的否定,串连起来又会变成什么呢。
脑内构想着谎言之膜轰然瓦解之时,眼前这个虚言症患者的绝望神情——
于是江之岛盾子再一次展露笑颜。
Fin
--------------------------------------------------------------------------------------------
——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全部全部全部都是骗你的唔噗噗绝望了吗快些快些坠入绝望吧唔噗噗这也是骗你的真的是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骗你的连『我』也是谎言之一哦。
……这句话既是罪木说的,又是盾子说的呢。
「为了否定前言而特意加上的否定,串连起来又会变成什么呢。」——这句的意思就是,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大概就是在Zero结束[盾子杀死松田]后,盾子再度失忆,被送去罪木所在的医院,然后这个时点上已经对盾子心怀爱意的罪木便说谎自己是松田,本以为自己在一直欺骗着盾子,结果没想到盾子根本没失忆,反倒是盾子在用「失忆了」这个巨大谎言将罪木自己团团包围……这样一个意味不明的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