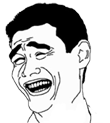一露吧 关注:93,334贴子:2,420,171
这是又一个六月,也是再一个的初六。
她手扶窗棂,静默地望向窗外。
青山依旧,绵延无边。
她看了片刻,慢慢掉转目光。
这确是极特殊的一个日子,只可惜这特殊性算不得持久,四年前,便已被她生生掐断。
她本意大抵不是如此,以至于今日猛然再见他,总有些恍惚。
他已是如此模样了吗?竟穿上了他素来不喜的儒生袍子。只是朗眉星目,总是去不掉那股子意气风发。
她坐回紫檀木的桌前,右手无意识地不断划过上面细密精巧的花纹,借由它自带的清雅馨香以及指尖连续不断的凹凸感来催醒自己的神智。
她今日如此作为实是不妥,直逼落荒而逃。
真真狼狈。
她本应得体的微笑作答,福身而去,只当真的是萍水相逢,而不是如此这般,不论如何去评鉴都差强人意。
毕竟这本是她一手促成的,左右不应由她露怯,且她本并不应当再与他相见,甚至狼狈败走。
她是不愿与自己的初衷相悖的。
不过也罢,真要说着,她算不得极令人走心的女子,左右不过是清秀,今日又这般的举止不当,他想来不会挂心。
她低垂着眼睫慢慢想着,面目平静,却忽然掉下滴泪来,砸在紫檀木面上,便是小小的一个水涡。
她不知当悲当喜,便只好无悲无喜。于是收起难得的小女儿娇态,慢慢站起身来。
六月初六,也不过是个天高云淡的日子。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这厢,他久违的失眠了。
原因不算复杂,不过是他难以接受。
因为他脑子里总是浮出那人的眼睛来,大而美丽,却既怨又恨。
这是为何?他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问题,却总也寻不出答案。他长得总不算丑的,此番作为虽然粗野了些,也不至于到了登徒子,那么她又是何故,竟然满眼的惊疑怨怼。
良久无果,他于是再翻个身,决定舍掉这个问题,又似乎想起些别的,面上却是一红。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定是一见钟情了。
虽然他不过初次见她,而她却表现出那般不知缘由的惊愕与恨意,但他仍是喜欢上了。
又不是少年了,真是!他觉着老脸一红,暗暗骂了一句。
这是多么久违的心动呢?他并没有算过,但在这般好的春光得以喜欢上这般的一个人,他竟然莫名欢喜。
而想及这儿,他却忽然又起了别的心思。
他忽然想起了他年少的钦慕之人。
其实现下想想,他不过是图个由头,毕竟是那般血气方刚的年纪,对什么都是好奇着的,而双方又觉得门当户对,便也就半推半就了。细说起来真算不得喜欢,但不知为何,他分明已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却总模糊不掉她残存的那点印象。
因为他总觉得有个女声在他耳边回响--
--“你啊,有个顶喜欢的人,她紫发橙瞳,面灿桃李,机敏乖巧,活泼可人,而耳后那条丝带,红的正衬她的面颊。”
其实他觉得那人是说错了,因为他喜欢的人有一头柔顺的黑发,那瞳孔也是紫色的,在阳光下如同西域美酒般剔透。且他总觉着她似乎还说了什么,却模糊的厉害,如何也记不起。
他始终记着,那声音温柔笃定,却总有一丝苍凉,而他对那阔别许久的青梅仍保有些许记忆,多半也是托了这个的福。
所有的念头都闪的极快,不多时便已消失的毫无踪迹。他眨眨眼,侧过身子,想的却已是如何去打听那人的名姓。
她喜着素色,身段玲珑,还善用工笔,啊,还有便是那把绘着桃花的油纸伞,可莫忘了。
他慢慢梳理着那惊鸿一瞥,不知餍足。
桃花伞,伞,桃花。
他毫无意义地将这个词拆的精细,不断念叨着,终于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只他仍在轻轻呢喃。
桃花伞,桃花。
桃花…
她手扶窗棂,静默地望向窗外。
青山依旧,绵延无边。
她看了片刻,慢慢掉转目光。
这确是极特殊的一个日子,只可惜这特殊性算不得持久,四年前,便已被她生生掐断。
她本意大抵不是如此,以至于今日猛然再见他,总有些恍惚。
他已是如此模样了吗?竟穿上了他素来不喜的儒生袍子。只是朗眉星目,总是去不掉那股子意气风发。
她坐回紫檀木的桌前,右手无意识地不断划过上面细密精巧的花纹,借由它自带的清雅馨香以及指尖连续不断的凹凸感来催醒自己的神智。
她今日如此作为实是不妥,直逼落荒而逃。
真真狼狈。
她本应得体的微笑作答,福身而去,只当真的是萍水相逢,而不是如此这般,不论如何去评鉴都差强人意。
毕竟这本是她一手促成的,左右不应由她露怯,且她本并不应当再与他相见,甚至狼狈败走。
她是不愿与自己的初衷相悖的。
不过也罢,真要说着,她算不得极令人走心的女子,左右不过是清秀,今日又这般的举止不当,他想来不会挂心。
她低垂着眼睫慢慢想着,面目平静,却忽然掉下滴泪来,砸在紫檀木面上,便是小小的一个水涡。
她不知当悲当喜,便只好无悲无喜。于是收起难得的小女儿娇态,慢慢站起身来。
六月初六,也不过是个天高云淡的日子。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这厢,他久违的失眠了。
原因不算复杂,不过是他难以接受。
因为他脑子里总是浮出那人的眼睛来,大而美丽,却既怨又恨。
这是为何?他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问题,却总也寻不出答案。他长得总不算丑的,此番作为虽然粗野了些,也不至于到了登徒子,那么她又是何故,竟然满眼的惊疑怨怼。
良久无果,他于是再翻个身,决定舍掉这个问题,又似乎想起些别的,面上却是一红。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定是一见钟情了。
虽然他不过初次见她,而她却表现出那般不知缘由的惊愕与恨意,但他仍是喜欢上了。
又不是少年了,真是!他觉着老脸一红,暗暗骂了一句。
这是多么久违的心动呢?他并没有算过,但在这般好的春光得以喜欢上这般的一个人,他竟然莫名欢喜。
而想及这儿,他却忽然又起了别的心思。
他忽然想起了他年少的钦慕之人。
其实现下想想,他不过是图个由头,毕竟是那般血气方刚的年纪,对什么都是好奇着的,而双方又觉得门当户对,便也就半推半就了。细说起来真算不得喜欢,但不知为何,他分明已记不清她的模样了,却总模糊不掉她残存的那点印象。
因为他总觉得有个女声在他耳边回响--
--“你啊,有个顶喜欢的人,她紫发橙瞳,面灿桃李,机敏乖巧,活泼可人,而耳后那条丝带,红的正衬她的面颊。”
其实他觉得那人是说错了,因为他喜欢的人有一头柔顺的黑发,那瞳孔也是紫色的,在阳光下如同西域美酒般剔透。且他总觉着她似乎还说了什么,却模糊的厉害,如何也记不起。
他始终记着,那声音温柔笃定,却总有一丝苍凉,而他对那阔别许久的青梅仍保有些许记忆,多半也是托了这个的福。
所有的念头都闪的极快,不多时便已消失的毫无踪迹。他眨眨眼,侧过身子,想的却已是如何去打听那人的名姓。
她喜着素色,身段玲珑,还善用工笔,啊,还有便是那把绘着桃花的油纸伞,可莫忘了。
他慢慢梳理着那惊鸿一瞥,不知餍足。
桃花伞,伞,桃花。
他毫无意义地将这个词拆的精细,不断念叨着,终于还是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只他仍在轻轻呢喃。
桃花伞,桃花。
桃花…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吧友嘲哪吒破百亿就是痴人说梦2897130
- 2JDG出师不利谁是最大罪人2432839
- 3米塔开发者表示中配太贵买不起2016448
- 4蛇年央视元宵晚会来了1956636
- 5哪吒2海外上座率暴打美国队长41707680
- 6乌克兰被特朗普抛弃气数已尽1248025
- 7深圳厂妹因黑眼圈过重被强制辞退991416
- 8梁文锋身家可能超越老黄820847
- 9山寨版哪吒2诈骗电影辣瞎眼776094
- 10贝林厄姆绝杀皇马拿下曼城77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