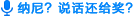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一)
到处都是血污,泥水,死人的残肢。屠戮血洗之后,只余秃鹰贪婪饥饿的目光。
充斥着恶臭和蛆虫的泥水坑里,是一个女婴。
入了夜,方圆四十里连人迹皆无,夜猫子凄厉的号声如同鬼哭。一个死村,仿佛千古荒野。
在这样的死村,出现的任何活物都会如同鬼魅吧。
就像他,玄色衣料在暗夜中流转异彩,趁着幽蓝的月华,诡谲动人。斗篷下,是两道寒芒,仿佛穿越了亘古,带着历史的悲戚。
女婴被裹在玄色斗篷里,连婴儿的轻哼声也没有。她靠着泥坑里混着血水的泥浆存活,肠胃都严重感染,到被他捞起时只余一息。
(二)
棘矜又一次顺利圆满完成任务。凡经他手的事总是极利落,一丝把柄下次都不见。
这一次的任务是押运私盐,这样的事棘矜每做一次,都像是白捡了一条命,他虽老成干练,行事得体,但不过二十岁的年纪,终究这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有些令人心惊。每次回来他都会直奔霓铩那里。这两年多来,他已经习惯了霓铩的倾听。霓铩是个姑娘,才十七岁,眉目之间自有一股冷意。按理说姑娘家的叫个如此戾气的名字有些奇怪,但这里的人无论男女都有这么一个听着就感觉杀气颇重的名字。
霓铩见到棘矜归来,眼中有了一丝喜色,但也一闪而逝。棘矜的性子淡漠,但每次见她,都变得善谈起来,讲述他外出执行任务的惊险时分,偶尔也带回一些趣事。霓铩注视着他的眼睛倾听,但只是无言。棘矜面对她,可以毫无顾忌的谈讲以释放压力。倒不是因为别的,只因霓铩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与人交际的能力。或许还因为棘矜觉得她与自己投缘,换句话,他瞧着她顺眼。
“这次比前些次还险,这段时间风声紧,官府在码头城门都设了暗探,当真的防不胜防。”
他一向谨慎,轻易不沾酒的。但今夜不知是不是放松了久绷的神经,需要定一定神。他轻呷一口酒,是女儿红,越州青瓷的杯。又缓缓开口,“但终究我做这些事是应该的,这样的恩情我该万死不辞的。”
他微微蹙眉,“这些话原不该说与你,但不知为何,我愿意与你说话。”
到处都是血污,泥水,死人的残肢。屠戮血洗之后,只余秃鹰贪婪饥饿的目光。
充斥着恶臭和蛆虫的泥水坑里,是一个女婴。
入了夜,方圆四十里连人迹皆无,夜猫子凄厉的号声如同鬼哭。一个死村,仿佛千古荒野。
在这样的死村,出现的任何活物都会如同鬼魅吧。
就像他,玄色衣料在暗夜中流转异彩,趁着幽蓝的月华,诡谲动人。斗篷下,是两道寒芒,仿佛穿越了亘古,带着历史的悲戚。
女婴被裹在玄色斗篷里,连婴儿的轻哼声也没有。她靠着泥坑里混着血水的泥浆存活,肠胃都严重感染,到被他捞起时只余一息。
(二)
棘矜又一次顺利圆满完成任务。凡经他手的事总是极利落,一丝把柄下次都不见。
这一次的任务是押运私盐,这样的事棘矜每做一次,都像是白捡了一条命,他虽老成干练,行事得体,但不过二十岁的年纪,终究这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有些令人心惊。每次回来他都会直奔霓铩那里。这两年多来,他已经习惯了霓铩的倾听。霓铩是个姑娘,才十七岁,眉目之间自有一股冷意。按理说姑娘家的叫个如此戾气的名字有些奇怪,但这里的人无论男女都有这么一个听着就感觉杀气颇重的名字。
霓铩见到棘矜归来,眼中有了一丝喜色,但也一闪而逝。棘矜的性子淡漠,但每次见她,都变得善谈起来,讲述他外出执行任务的惊险时分,偶尔也带回一些趣事。霓铩注视着他的眼睛倾听,但只是无言。棘矜面对她,可以毫无顾忌的谈讲以释放压力。倒不是因为别的,只因霓铩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与人交际的能力。或许还因为棘矜觉得她与自己投缘,换句话,他瞧着她顺眼。
“这次比前些次还险,这段时间风声紧,官府在码头城门都设了暗探,当真的防不胜防。”
他一向谨慎,轻易不沾酒的。但今夜不知是不是放松了久绷的神经,需要定一定神。他轻呷一口酒,是女儿红,越州青瓷的杯。又缓缓开口,“但终究我做这些事是应该的,这样的恩情我该万死不辞的。”
他微微蹙眉,“这些话原不该说与你,但不知为何,我愿意与你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