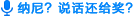经典小说配音吧 关注:4,030贴子:89,499
三月的天书都印错,竟无人知晓。
近郊山头染了雪迹,山腰的杜鹃与瘦樱仍然一派天真地等春。三月本来无庸置疑,只有我关心瑞雪与花季的争辩,就像关心生活的水潦能否允许生命的焚烧。但,人活得疲了,转烛于锱铢,或酒色,或一条百年老河养不养得起一只螃蟹?于是我也放胆地让自己疲着,圆滑地在言语厮杀的会议之后,用寒鸦的音色赞美:“这世界多么有希望啊!”然后,走。
直到一本陌生的诗集飘至眼前,印了一年仍然初版的冷诗,(我们是诗的后裔!)诗的序写于两年前,若回溯行文走句,该有四年,若还原至初孕的人生,或则六年,八年。于是,我做了生平第一件快事,将三家书店摆饰的集子买尽--原谅我鲁莽啊!陌生的诗人,所有不被珍爱的人生都应该高傲地绝版!
近郊山头染了雪迹,山腰的杜鹃与瘦樱仍然一派天真地等春。三月本来无庸置疑,只有我关心瑞雪与花季的争辩,就像关心生活的水潦能否允许生命的焚烧。但,人活得疲了,转烛于锱铢,或酒色,或一条百年老河养不养得起一只螃蟹?于是我也放胆地让自己疲着,圆滑地在言语厮杀的会议之后,用寒鸦的音色赞美:“这世界多么有希望啊!”然后,走。
直到一本陌生的诗集飘至眼前,印了一年仍然初版的冷诗,(我们是诗的后裔!)诗的序写于两年前,若回溯行文走句,该有四年,若还原至初孕的人生,或则六年,八年。于是,我做了生平第一件快事,将三家书店摆饰的集子买尽--原谅我鲁莽啊!陌生的诗人,所有不被珍爱的人生都应该高傲地绝版!
然而当我们把所有的集子同时翻到最后一页题曰最后一首情诗时,午后的雨丝正巧从帘缝蹑足而来。三月的驼云倾倒的是二月的水谷,正如薄薄的诗舟盛载着积年的乱麻。于是我轻轻地笑起来,文学,真是永不疲倦的流刑地啊!那些黥面的人,不必起解就自行前来招供、画押。因为,唯有此地允许罪愆者徐徐地申诉而后自行判刑,唯有此地,宁愿放纵不愿错杀。
原谅我把冷寂的清官朝服剪成合身的寻日布艺,把你的一品丝绣裁成放心事的暗袋,你娴熟的三行连韵与商簌体,到我手上变为缝缝补补的百衲图。安静些,三月的鬼雨,我要翻箱倒箧(qie)【语音里口误了不好意思…】,再裂一条无汗拭泪的巾帕。
原谅我把冷寂的清官朝服剪成合身的寻日布艺,把你的一品丝绣裁成放心事的暗袋,你娴熟的三行连韵与商簌体,到我手上变为缝缝补补的百衲图。安静些,三月的鬼雨,我要翻箱倒箧(qie)【语音里口误了不好意思…】,再裂一条无汗拭泪的巾帕。
约在医院门口见面,并且好好地晚餐。你的衣角仍飘荡着辛涩的药味,这应是最无菌的一次约会。可惜的,惨淡夜色让你看起来苍白,仿佛生与死的演绎仍鞭笞着你瘦而长的身躯。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星期见十三名儿童死去,你常说你已学会在面对病人死亡之时,让脑子一片空白,继续做一个饱餐、更浴、睡眠的无所谓的人。在早期,你所写的那首《白鹭鸶》诗里,曾雄壮地要求天地给你这一席白衣;白衣红里,你在数年之后《关渡手稿》这样写,恐怕,我是你的尸体衣裳,非婚礼华服,并且悄悄地后记着:“每次当病人危急时,我们明知无用,仍勉强做些急救的工作。其目的并非要救病人,而是来安慰家属。”
百度小说人气榜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王楚钦4-0张本智和夺冠2528880
- 2王曼昱4-3陈幸同夺冠1827112
- 3前体操冠军吴柳芳回应擦边争议1679427
- 4PRX2:1战胜EDG1410032
- 5卫生巾新国标正在起草1305650
- 6IG新赛季阵容曝光915744
- 7曝双城之战梅尔为新英雄780252
- 8诗词教育大家叶嘉莹去世559724
- 9曝Peyz加入LNG511812
- 10湖人25分惨败掘金384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