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你会看见一向文静的她,熟练地抽着烟。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一向浮躁的他,开了一家咖啡厅。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视分数如粪土的她,打着不及格的儿子。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捣蛋的他,穿上了警服。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抨击制度腐朽
党国无能的她,默默地站在政府门前宣读公告。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一向一毛不拔的他,往募捐箱内投入一叠大钞。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成绩最优异的她,住在十尺见方的老房子里。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喊着要征服世界的他,坐在电脑前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温文儒雅的她,上演着泼妇骂街的光景。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出手阔绰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碗。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为沉默的她,毅然站上演讲台。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弱不禁风的他,熟练地使出一记过肩摔。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胆小如鼠的她,冲上了前线。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为正义的他,披上了囚服。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美丽的她,眼角已刻上了鱼尾纹。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熟悉的他,话语中已充满了陌生…
朋友啊,你青春的稚嫩,是何人帮你抹去?
转眼间什么都变了,没有谁能保持本心,只能任凭岁月无情地刻下疤痕。
到那时,
曾经熟悉的你,又会变得如何呢?
到那时,
那一颗炽热的心是否还依旧呢?
到那时,
挖掘机技术蓝翔是否还是最强呢?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一向浮躁的他,开了一家咖啡厅。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视分数如粪土的她,打着不及格的儿子。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捣蛋的他,穿上了警服。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抨击制度腐朽
党国无能的她,默默地站在政府门前宣读公告。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一向一毛不拔的他,往募捐箱内投入一叠大钞。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成绩最优异的她,住在十尺见方的老房子里。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喊着要征服世界的他,坐在电脑前无所事事地度过一生。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温文儒雅的她,上演着泼妇骂街的光景。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出手阔绰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破碗。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为沉默的她,毅然站上演讲台。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弱不禁风的他,熟练地使出一记过肩摔。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胆小如鼠的她,冲上了前线。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为正义的他,披上了囚服。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美丽的她,眼角已刻上了鱼尾纹。
多年以后,你会看见最熟悉的他,话语中已充满了陌生…
朋友啊,你青春的稚嫩,是何人帮你抹去?
转眼间什么都变了,没有谁能保持本心,只能任凭岁月无情地刻下疤痕。
到那时,
曾经熟悉的你,又会变得如何呢?
到那时,
那一颗炽热的心是否还依旧呢?
到那时,
挖掘机技术蓝翔是否还是最强呢?


 这人啊一上等级就缺经验
这人啊一上等级就缺经验 过去一天三遍地发帖
过去一天三遍地发帖 麻烦!
麻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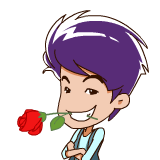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有了发图赚经验
有了发图赚经验 一张图顶过去五个贴
一张图顶过去五个贴 一天一图,效果还不错
一天一图,效果还不错


 代排位
代排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