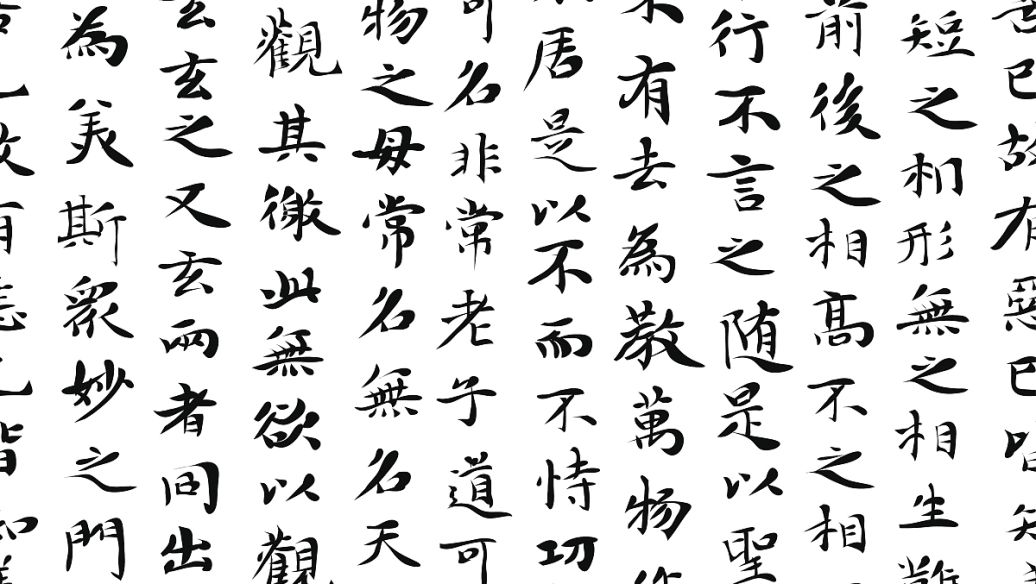严冬、酷寒、冰山、雪原。
银装素裹,雪挂冰封。莽莽天间唯见一片凄愁惨淡的白。北风如刀,霜华飞舞,夹杂着薄薄的烟霭和苍茫的气色;林瘦山寒,雪粉腾扬,似在山林间吹围起一层白幔。
在初晓的灰色天空下,淡云一层一层褪去,慢慢露出一片华晕。忽而,明光耀眼,映出银龙玉海,鳞鳞缟素,将群峦刻画成锯齿形。那陡峭的山崖上坠挂着长长的、尖利的、经年不化的冰柱,就如参差交错的狼牙。
※※※
许紫亭一身白袍,面色木然,独立于长白山脚下。
冷风刺骨,仍在刮个不休,怒吼着卷起雪粒,呼出悲惨的尖啸。大雪虽已停止,过膝的雪层,铺遮了整个峰巅。
令人惊奇的是,他身边的雪上却没见到脚印,只有极浅极淡的一道痕迹在风雪的遮掩下逐渐消散。
看来,他已这般静静站了很久,而且似乎还要一直如此站立下去。
凛冽的寒风将他的白袍轻轻掀起,露出贴身的赤色锦衣,在一片晶澈莹素中显出一抹触目惊心的艳红。而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他腰间悬挂的那柄长剑。
——剑无鞘,长三尺三寸,剑锷处镶刻着一枚醒目的蓝宝石。微蓝的剑芒在剔透的雪色掩映下,那两长的血槽沁出慑人的寒光。铁木所制的黝黑剑柄上没有任何华丽的饰物,只用撕成细条的粗布层层裹扎起来,可那青朴的颜色更衬得剑锋杀气逼人。
看来,这不但是一柄好剑,而且必定是一柄长于杀人的好剑。
※※※
江湖上认得许紫亭的人并不多,但认得这柄剑的人却绝对不少。
长白山掌门、东北第一世家许家大少爷许紫亭最有名的,不是他仗义疏财、友遍天下,也不是家世渊源、富甲一方,而是他掌中的那一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的“映雪剑”和四十九路“荡雪剑法”。
十九岁时,他的人与他的剑就已名满江湖。如今,虽然他已近不惑之年,但威望却更高,剑的锋芒也更盛。
不过,经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许紫亭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态疏狂、心绪激昂、动不动就与人争一时之气的倨傲少年,而是慢慢收敛起锋锐,一心坐享家财,拥妻教子。事实上,他已足足有五年,再也没有与任何人动武斗狠了。
可是,在一个如此清冷寒凉的早上,许紫亭不在家中享福,来到这冰山脚下却又是为了什么?
※※※
许紫亭的身子纹丝不动,一脸肃穆,右手搭在“映雪剑”的剑柄上,双目偶尔垂顾,便重又直勾勾望向山路,似正在等待着什么人。看他一脸大异往常的紧张神色,似乎来人会对他不利。
谁会有这么大胆子,谁又能有这么强的实力,敢于在这长白山脚下找长白掌门许紫亭的麻烦?
突然,一阵急促的风雪骤然飙来,令人目眩神迷。
许紫亭微微侧头,避开这突如其来的蹊跷狂风。这一刻,他虽然闭上了眼睛,耳朵却警醒起来。
他虽已久不对敌,但这些年来却从没放下过赖以成名的“映雪剑”,作为一个一流剑客,他仍具备超级敏锐的洞察力。
只听一种怪异的声音从那飘荡风雪的悲啸中由远至近传来,就似是有什么重物正在雪上缓缓滚动着。伴随那阵怪异滚动声一并袭来的,还有一对轻轻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绝对不算沉重,可是在许紫亭耳中,却不啻于远方正行来一头来自洪荒远古的巨大怪兽。
许紫亭的腰在刹那间挺得笔直,握在剑柄上的右手因用力而发白,双目在瞬间泛起一抹光亮,直直向迷雾般的风雪中探射而去。
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大雪球正慢慢、慢慢朝他滚过来。
那大雪球在深可没膝的雪上滚动不止,直到许紫亭的面前时,才忽然停了下来。猛然,一张胖脸从雪球后突兀冒了出来,一双小眼寒光隐现,笑嘻嘻的脸上两堆肥肉上下跳动:“许兄早,许兄好。”
这场面本来颇有些滑稽,可许紫亭却不由自主退开半步,眼中现出警惕的神色:“来的可是应兄么?久仰大名,许某这厢有礼了。”
“好说好说。”那胖子嘿嘿一笑,一双粗壮的大腿踢踏着将积雪卷扬而起。
他先将大雪球摆放平稳,这才喘口粗气道:“许掌门倒是起来得早,可吃了早点么?”看他那一脸熟络的样子,倒似是与许紫亭相交已久,此刻只是浑若平常和熟人打个招呼而已。
只是那胖子一口粗气方才重重吐出,大雪球的上半端便被如斩肢断首般蓦然割裂飞起,落入雪中。那断面平整光滑,就似是有把快刀从雪球上齐齐削过一般。
“应兄好精深的内力。”许紫亭脸现惊容,勉强笑道,“出来得有些着急,这早点倒不曾吃过。其实应兄不远千里来到长白山,原该是许某做东,好好招待你一番的。”
“许掌门太客气了。害你在这么冷的天一大早便出门,我应千钟原是该向你赔罪才是。好在我做了十几年的厨子,吃饭的家伙倒是随身带着的……”
就见那巨大的雪团上端被削去,露出一口黑如沉墨的大铁箱来。话音未毕,那姓应的胖子口中说话,双手却是不停,变戏法一般不断从大雪团中取出一大堆坛坛罐罐。
——那铁箱里面却是油盐酱醋等各式调料,再拿出冻鸡、冻肉、各种蔬菜盘碟,末了又取出一把大菜刀,乒乒乓乓切割起来,仿佛那雪球中所藏的不是一口铁箱,而是一方案板。
只见应千钟一双手左右腾挪,大菜刀上下翻飞,却不与铁箱发出半点碰撞声。快得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铁箱上已排列着五六样精致的小菜。
想必谁也想象不到,那胖得似是连五根指头都连在一处的双手竟会是如此的巧妙灵动。
身处如此寒冷的天气,许紫亭却觉自己的额头上已渗出汗珠:若是这双手击打在身上、若是这把刀割在咽喉上,又会是如何结果呢?
应千钟满意拍手一笑:“若是许掌门看得起,请务必尝尝我的手艺。”他指指其中一盘菜,“尤其是这味‘狼子野心’,材料可是我昨夜刚刚从一头怀孕母狼的肚中取出的三只小狼崽,实在是新鲜得紧……”
许紫亭强忍住胸口的恶心,小心赔笑道:“应兄艺高胆大,这味菜大概亦只有你方能做得出来。”
应千钟哈哈大笑,复又奇怪打量了许紫亭一眼:“这附近埋伏的长白十八弟子原本都眼睁睁准备看着自家的许掌门要如何大展神威,可是你此刻竟然对我这般大拍马屁,也不怕坠了掌门的威风么?”
许紫亭胸口如遭重击,万未想到自己的十八名得意弟子埋伏于侧,竟然会被对方一口道破,而看他浑若无事的样子,分明是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良久,许紫亭方才讪讪自嘲道:“应兄大驾光临,长白上下自然皆想一睹风采。”
应千钟猛然深吸一口气,那盘“狼子野心”中一颗狼心便蓦然跳入他口中。待闭上眼细细咀嚼一番,他方长舒一口气,摇头晃脑道:“味辛而涩,肉滑而韧,如此方有塞外之风。”说完后,又睁开一双小眼,阴森森望向许紫亭,“咦,许掌门的手为何在发抖?”
银装素裹,雪挂冰封。莽莽天间唯见一片凄愁惨淡的白。北风如刀,霜华飞舞,夹杂着薄薄的烟霭和苍茫的气色;林瘦山寒,雪粉腾扬,似在山林间吹围起一层白幔。
在初晓的灰色天空下,淡云一层一层褪去,慢慢露出一片华晕。忽而,明光耀眼,映出银龙玉海,鳞鳞缟素,将群峦刻画成锯齿形。那陡峭的山崖上坠挂着长长的、尖利的、经年不化的冰柱,就如参差交错的狼牙。
※※※
许紫亭一身白袍,面色木然,独立于长白山脚下。
冷风刺骨,仍在刮个不休,怒吼着卷起雪粒,呼出悲惨的尖啸。大雪虽已停止,过膝的雪层,铺遮了整个峰巅。
令人惊奇的是,他身边的雪上却没见到脚印,只有极浅极淡的一道痕迹在风雪的遮掩下逐渐消散。
看来,他已这般静静站了很久,而且似乎还要一直如此站立下去。
凛冽的寒风将他的白袍轻轻掀起,露出贴身的赤色锦衣,在一片晶澈莹素中显出一抹触目惊心的艳红。而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却是他腰间悬挂的那柄长剑。
——剑无鞘,长三尺三寸,剑锷处镶刻着一枚醒目的蓝宝石。微蓝的剑芒在剔透的雪色掩映下,那两长的血槽沁出慑人的寒光。铁木所制的黝黑剑柄上没有任何华丽的饰物,只用撕成细条的粗布层层裹扎起来,可那青朴的颜色更衬得剑锋杀气逼人。
看来,这不但是一柄好剑,而且必定是一柄长于杀人的好剑。
※※※
江湖上认得许紫亭的人并不多,但认得这柄剑的人却绝对不少。
长白山掌门、东北第一世家许家大少爷许紫亭最有名的,不是他仗义疏财、友遍天下,也不是家世渊源、富甲一方,而是他掌中的那一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的“映雪剑”和四十九路“荡雪剑法”。
十九岁时,他的人与他的剑就已名满江湖。如今,虽然他已近不惑之年,但威望却更高,剑的锋芒也更盛。
不过,经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许紫亭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态疏狂、心绪激昂、动不动就与人争一时之气的倨傲少年,而是慢慢收敛起锋锐,一心坐享家财,拥妻教子。事实上,他已足足有五年,再也没有与任何人动武斗狠了。
可是,在一个如此清冷寒凉的早上,许紫亭不在家中享福,来到这冰山脚下却又是为了什么?
※※※
许紫亭的身子纹丝不动,一脸肃穆,右手搭在“映雪剑”的剑柄上,双目偶尔垂顾,便重又直勾勾望向山路,似正在等待着什么人。看他一脸大异往常的紧张神色,似乎来人会对他不利。
谁会有这么大胆子,谁又能有这么强的实力,敢于在这长白山脚下找长白掌门许紫亭的麻烦?
突然,一阵急促的风雪骤然飙来,令人目眩神迷。
许紫亭微微侧头,避开这突如其来的蹊跷狂风。这一刻,他虽然闭上了眼睛,耳朵却警醒起来。
他虽已久不对敌,但这些年来却从没放下过赖以成名的“映雪剑”,作为一个一流剑客,他仍具备超级敏锐的洞察力。
只听一种怪异的声音从那飘荡风雪的悲啸中由远至近传来,就似是有什么重物正在雪上缓缓滚动着。伴随那阵怪异滚动声一并袭来的,还有一对轻轻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绝对不算沉重,可是在许紫亭耳中,却不啻于远方正行来一头来自洪荒远古的巨大怪兽。
许紫亭的腰在刹那间挺得笔直,握在剑柄上的右手因用力而发白,双目在瞬间泛起一抹光亮,直直向迷雾般的风雪中探射而去。
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大雪球正慢慢、慢慢朝他滚过来。
那大雪球在深可没膝的雪上滚动不止,直到许紫亭的面前时,才忽然停了下来。猛然,一张胖脸从雪球后突兀冒了出来,一双小眼寒光隐现,笑嘻嘻的脸上两堆肥肉上下跳动:“许兄早,许兄好。”
这场面本来颇有些滑稽,可许紫亭却不由自主退开半步,眼中现出警惕的神色:“来的可是应兄么?久仰大名,许某这厢有礼了。”
“好说好说。”那胖子嘿嘿一笑,一双粗壮的大腿踢踏着将积雪卷扬而起。
他先将大雪球摆放平稳,这才喘口粗气道:“许掌门倒是起来得早,可吃了早点么?”看他那一脸熟络的样子,倒似是与许紫亭相交已久,此刻只是浑若平常和熟人打个招呼而已。
只是那胖子一口粗气方才重重吐出,大雪球的上半端便被如斩肢断首般蓦然割裂飞起,落入雪中。那断面平整光滑,就似是有把快刀从雪球上齐齐削过一般。
“应兄好精深的内力。”许紫亭脸现惊容,勉强笑道,“出来得有些着急,这早点倒不曾吃过。其实应兄不远千里来到长白山,原该是许某做东,好好招待你一番的。”
“许掌门太客气了。害你在这么冷的天一大早便出门,我应千钟原是该向你赔罪才是。好在我做了十几年的厨子,吃饭的家伙倒是随身带着的……”
就见那巨大的雪团上端被削去,露出一口黑如沉墨的大铁箱来。话音未毕,那姓应的胖子口中说话,双手却是不停,变戏法一般不断从大雪团中取出一大堆坛坛罐罐。
——那铁箱里面却是油盐酱醋等各式调料,再拿出冻鸡、冻肉、各种蔬菜盘碟,末了又取出一把大菜刀,乒乒乓乓切割起来,仿佛那雪球中所藏的不是一口铁箱,而是一方案板。
只见应千钟一双手左右腾挪,大菜刀上下翻飞,却不与铁箱发出半点碰撞声。快得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铁箱上已排列着五六样精致的小菜。
想必谁也想象不到,那胖得似是连五根指头都连在一处的双手竟会是如此的巧妙灵动。
身处如此寒冷的天气,许紫亭却觉自己的额头上已渗出汗珠:若是这双手击打在身上、若是这把刀割在咽喉上,又会是如何结果呢?
应千钟满意拍手一笑:“若是许掌门看得起,请务必尝尝我的手艺。”他指指其中一盘菜,“尤其是这味‘狼子野心’,材料可是我昨夜刚刚从一头怀孕母狼的肚中取出的三只小狼崽,实在是新鲜得紧……”
许紫亭强忍住胸口的恶心,小心赔笑道:“应兄艺高胆大,这味菜大概亦只有你方能做得出来。”
应千钟哈哈大笑,复又奇怪打量了许紫亭一眼:“这附近埋伏的长白十八弟子原本都眼睁睁准备看着自家的许掌门要如何大展神威,可是你此刻竟然对我这般大拍马屁,也不怕坠了掌门的威风么?”
许紫亭胸口如遭重击,万未想到自己的十八名得意弟子埋伏于侧,竟然会被对方一口道破,而看他浑若无事的样子,分明是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良久,许紫亭方才讪讪自嘲道:“应兄大驾光临,长白上下自然皆想一睹风采。”
应千钟猛然深吸一口气,那盘“狼子野心”中一颗狼心便蓦然跳入他口中。待闭上眼细细咀嚼一番,他方长舒一口气,摇头晃脑道:“味辛而涩,肉滑而韧,如此方有塞外之风。”说完后,又睁开一双小眼,阴森森望向许紫亭,“咦,许掌门的手为何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