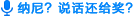天以立秋,万物都开始凋谢。郊外的天更是凄凉,到唯独那最偏远的一家,庭院内生机盎然。我向人打听那家四季如春的道儿,人们只说;那家住着一个俄/国人,成天对着一颗古树发呆。我很好奇,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郊外去拜访。当我按门铃时,一个很高大的斯拉夫男人已经开了门。
男人有着白金色的头发,红宝石似的眼睛冷冷地打探着我,我感觉他像是在盯唾手可得的猎物。男人脖颈处围着一条破旧发黄的围巾,身着正装,背后披着一个黑色大风衣。
“请进吧。”
男人的声音与外貌完全成反比,他的声音干净不含一丝杂碎,犹如白雪一样透彻你的心房。我被声音愣住了一会儿,但很快说:“谢谢您,先生。”屋内没有我想象的西式风格,而是完完全全的东式。我脱下被泥土弄脏的鞋子,小心翼翼的跟在男人的后面。
“王黯,出来。有……咳咳客人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相貌清秀的少年夺门而出。少年表情厌恶,让我觉到强烈的压迫感。“还真是好久没有客人来了呢,维克多?”少年朝男人露出微笑,我认为那微笑是变相的讽刺我,因为少年在语句里加重了【好久】和【维克多】这两个词。接着,少年又说:“我当年真应该像往常一样扮鬼吓走你,我去要清静。”
男人蹙眉,叹了口气说道:“可你没有。”又转头对我说:“这……位先生,请坐吧,不必拘谨。”少年似乎拿男人没了法子,搀扶着男人在另一边坐下。
“你们的感情真好。”
我试着缓解下这尴尬的气氛,说道。可少年却冷哼道:“谁和这个欠扁的家伙感情好,就因为他……”男人瞪了他一眼,少年不说话了。“您是想咳咳……看我的庭院吧,这位先生。”男人起身,带我来到他的后院。
这不是一般的美,美的让人无法形容。
男人坐在一边,看着在庭院中间的那颗老古树,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少年站在他身旁,不断抚摸着男人消瘦的脸庞。
【你想听我们的故事吗?】
【当然。】
过了几天之后,我离开了那个四季如春的屋子。我像是着了魔似的,奋笔疾书的写一篇长篇小说。我几乎把我一生所用之词加在小说里面,让这部小说读起来动人心弦。终于,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完成这部小说。小说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追捧,当人们在问我准不准备写下一部?
我笑着回答: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就是死了。
男人有着白金色的头发,红宝石似的眼睛冷冷地打探着我,我感觉他像是在盯唾手可得的猎物。男人脖颈处围着一条破旧发黄的围巾,身着正装,背后披着一个黑色大风衣。
“请进吧。”
男人的声音与外貌完全成反比,他的声音干净不含一丝杂碎,犹如白雪一样透彻你的心房。我被声音愣住了一会儿,但很快说:“谢谢您,先生。”屋内没有我想象的西式风格,而是完完全全的东式。我脱下被泥土弄脏的鞋子,小心翼翼的跟在男人的后面。
“王黯,出来。有……咳咳客人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个相貌清秀的少年夺门而出。少年表情厌恶,让我觉到强烈的压迫感。“还真是好久没有客人来了呢,维克多?”少年朝男人露出微笑,我认为那微笑是变相的讽刺我,因为少年在语句里加重了【好久】和【维克多】这两个词。接着,少年又说:“我当年真应该像往常一样扮鬼吓走你,我去要清静。”
男人蹙眉,叹了口气说道:“可你没有。”又转头对我说:“这……位先生,请坐吧,不必拘谨。”少年似乎拿男人没了法子,搀扶着男人在另一边坐下。
“你们的感情真好。”
我试着缓解下这尴尬的气氛,说道。可少年却冷哼道:“谁和这个欠扁的家伙感情好,就因为他……”男人瞪了他一眼,少年不说话了。“您是想咳咳……看我的庭院吧,这位先生。”男人起身,带我来到他的后院。
这不是一般的美,美的让人无法形容。
男人坐在一边,看着在庭院中间的那颗老古树,一看就是好长时间。少年站在他身旁,不断抚摸着男人消瘦的脸庞。
【你想听我们的故事吗?】
【当然。】
过了几天之后,我离开了那个四季如春的屋子。我像是着了魔似的,奋笔疾书的写一篇长篇小说。我几乎把我一生所用之词加在小说里面,让这部小说读起来动人心弦。终于,在第五年的时候我完成这部小说。小说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追捧,当人们在问我准不准备写下一部?
我笑着回答:生命只有一次,死了,就是死了。


 for u
for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