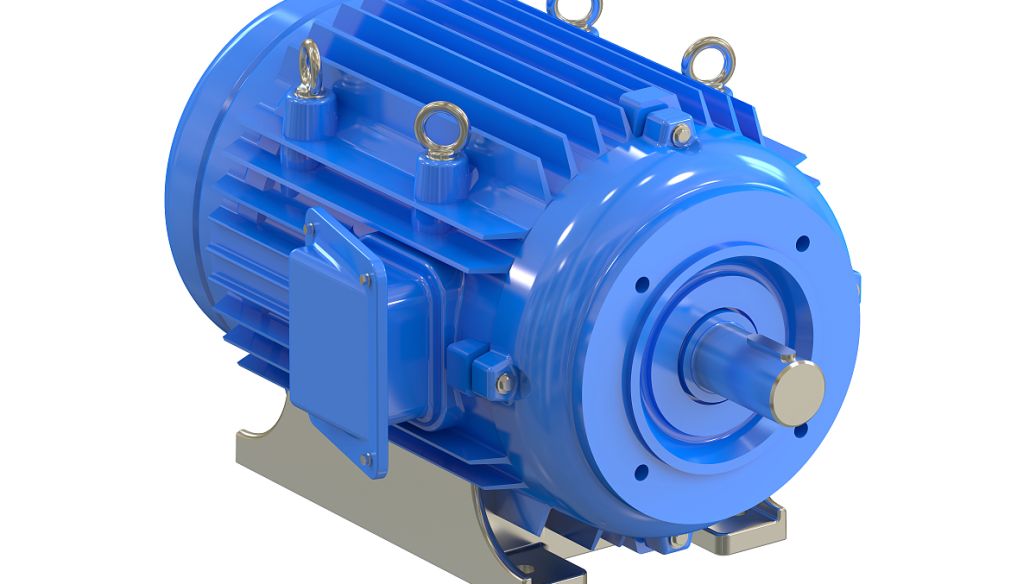伊万的杯子里装着不加方糖的红茶,他又一次登上207次通往莫/斯/科的火车。每当他登上列车时,他总能回想起尼古拉二世当年是多么兴奋的向他宣布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铁路,他的小女儿眼里闪着期待的光,望着她的父亲,拽着伊万的衣角问,“他是你见过的,最好的沙皇吗?”
他怀念往事的思绪被更上一层的喧闹声打扰,人群不安的躁动起来,带着白色帽子的导游高声提醒人们跟紧队伍。
当伊万登上列车安顿好一切,他倚在软绵的枕头时,早已入冬的列车上将暖气开的很足。他阖上眼思考着到达莫/斯/科以后的行程。然而有人将伊万身边的被子拽过来盖在他身上。
伊万隐约感觉那是一双肉呼呼的小手,那双小手的温暖和着列车上的暖气,安静的睡去。
他浅浅的一觉醒来,对面下铺的小孩子抱着他外祖母的胳膊,看着她外祖母的填字游戏,一边猜测着几个俄语单词,一边冲伊万微笑。
那个老妇人撕开了一包糖果,她就像是其他俄/罗/斯女人一样,喜欢可口而且能抵御严寒的高热量甜食。她将两颗糖递给了伊万,脸上慈祥的微笑让她的脸看起来多少有些亲切。伊万觉得似乎在很久以前见过她。
他试问道:“我们以前在喀山大学见过面吗?柳达。”每个国/家基本上都能记住子民们的名字,尽管世人也知道俄/罗/斯人的名字很长,但是他依旧能记得,他依旧不会忘。
她点点头,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减,牵了伊万的手,她的手掌足够暖和,足以抵挡列车外早已到达的冰点,“我的祖/国,您看,时间过得真快。”她叹道,却没有与故人再多说几句。伊万记得他们在喀/山大学相遇相识,还交换过许多信件,也大概是因为她拥有了更多想珍惜的人,信件也终于在某一天停下了。
鄂/木/斯/克的月台,夕阳正照在他们身上。
伊万裹紧了自己的围巾,他突然很难过。“快到您的生日了吧?生日快乐。”她温柔的微笑着,“再见了,我的祖/国。”她手中握着她孙子的小手,随即离去。
在伊万的记忆里,她的背影这一如她年轻时的样子。
我们最终告别,在我们相遇的时候。
他怀念往事的思绪被更上一层的喧闹声打扰,人群不安的躁动起来,带着白色帽子的导游高声提醒人们跟紧队伍。
当伊万登上列车安顿好一切,他倚在软绵的枕头时,早已入冬的列车上将暖气开的很足。他阖上眼思考着到达莫/斯/科以后的行程。然而有人将伊万身边的被子拽过来盖在他身上。
伊万隐约感觉那是一双肉呼呼的小手,那双小手的温暖和着列车上的暖气,安静的睡去。
他浅浅的一觉醒来,对面下铺的小孩子抱着他外祖母的胳膊,看着她外祖母的填字游戏,一边猜测着几个俄语单词,一边冲伊万微笑。
那个老妇人撕开了一包糖果,她就像是其他俄/罗/斯女人一样,喜欢可口而且能抵御严寒的高热量甜食。她将两颗糖递给了伊万,脸上慈祥的微笑让她的脸看起来多少有些亲切。伊万觉得似乎在很久以前见过她。
他试问道:“我们以前在喀山大学见过面吗?柳达。”每个国/家基本上都能记住子民们的名字,尽管世人也知道俄/罗/斯人的名字很长,但是他依旧能记得,他依旧不会忘。
她点点头,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减,牵了伊万的手,她的手掌足够暖和,足以抵挡列车外早已到达的冰点,“我的祖/国,您看,时间过得真快。”她叹道,却没有与故人再多说几句。伊万记得他们在喀/山大学相遇相识,还交换过许多信件,也大概是因为她拥有了更多想珍惜的人,信件也终于在某一天停下了。
鄂/木/斯/克的月台,夕阳正照在他们身上。
伊万裹紧了自己的围巾,他突然很难过。“快到您的生日了吧?生日快乐。”她温柔的微笑着,“再见了,我的祖/国。”她手中握着她孙子的小手,随即离去。
在伊万的记忆里,她的背影这一如她年轻时的样子。
我们最终告别,在我们相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