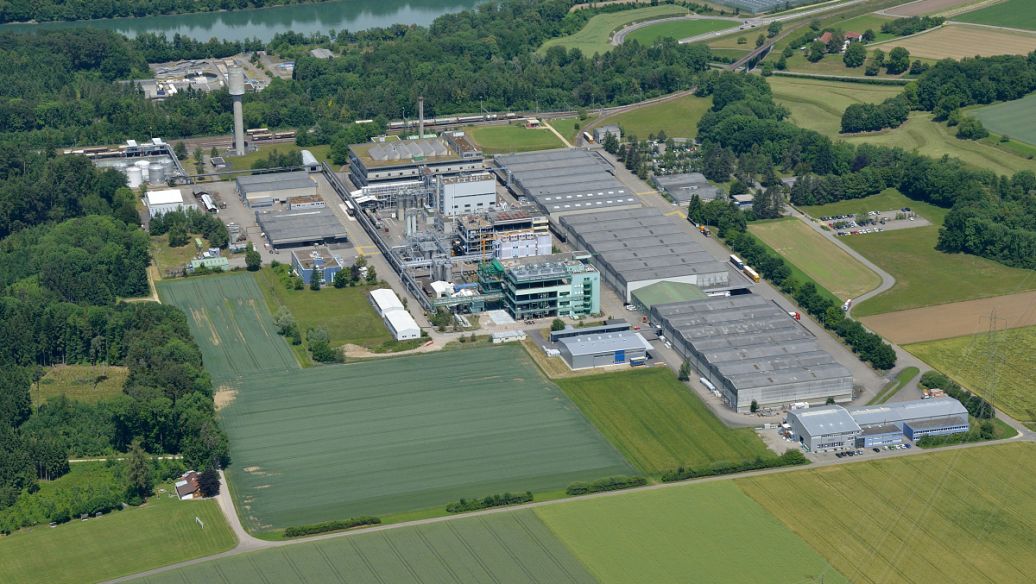跟Yuki分手后的一个月里,我一直处于“如遭雷亟”的状态,整天阴沉着一张脸,眼袋大得都快到下巴了。我的情绪也十分不稳定,暴躁易怒,知情的朋友能理解,不知情的朋友就觉得我疯了。
话说白人本身是很注意不去打听别人的隐私的,但Rachel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是很close的朋友,所以她有义务关心我。她三番四次的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抑郁成这样。
那时,Yuki的事还像根针似的扎在我脑子里,想到提到就会一阵刺痛,我不愿多说。再者,不管怎么看,当了一次非传统绿帽男,这也不是能在妹子面前拿得出手的光辉事迹,我是很抗拒告诉Rachel的。
临近考试的某一天,我和Rachel上班时,她终于受不了我的颓唐和抗拒交流,第一次很情绪化的对我发脾气,觉得我对她保留太多,不把她当可以分享和支持的好朋友。
我那时还年轻(21岁),经历得太少,又强撑了太久,Rachel这种关怀式的发脾气一下戳破了我的伪装,我叹息着,十分没出息的流泪了。
话说白人本身是很注意不去打听别人的隐私的,但Rachel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是很close的朋友,所以她有义务关心我。她三番四次的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抑郁成这样。
那时,Yuki的事还像根针似的扎在我脑子里,想到提到就会一阵刺痛,我不愿多说。再者,不管怎么看,当了一次非传统绿帽男,这也不是能在妹子面前拿得出手的光辉事迹,我是很抗拒告诉Rachel的。
临近考试的某一天,我和Rachel上班时,她终于受不了我的颓唐和抗拒交流,第一次很情绪化的对我发脾气,觉得我对她保留太多,不把她当可以分享和支持的好朋友。
我那时还年轻(21岁),经历得太少,又强撑了太久,Rachel这种关怀式的发脾气一下戳破了我的伪装,我叹息着,十分没出息的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