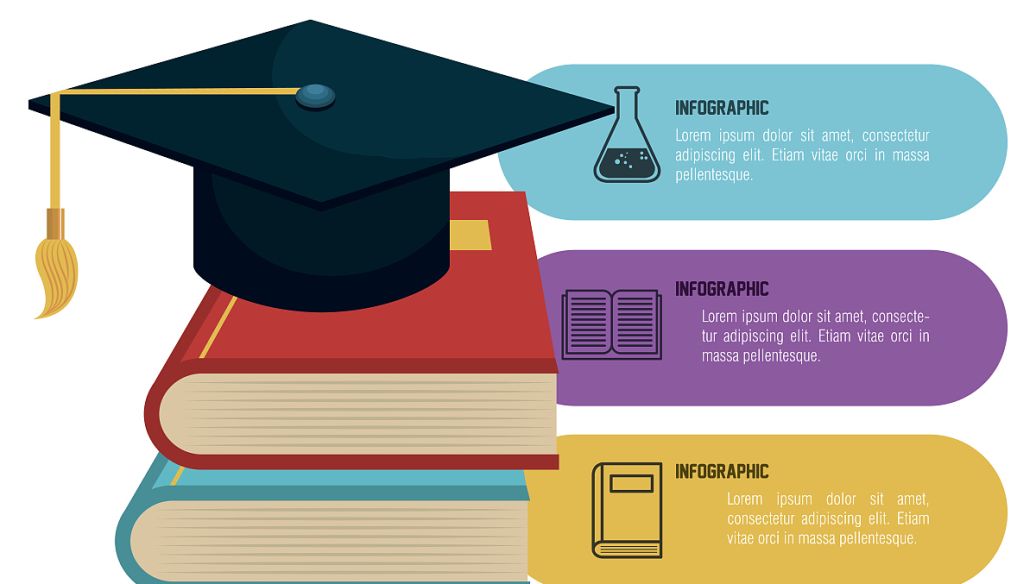红瞳青年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一点……很重要吗?”以赛亚的嘴角微微上扬。
“没什么,”帝人答道,“我这具单薄的躯壳并不足以安放任何伟大的东西,而我所爱着的自己则理应是某种本该抵达上帝的领域的东西,所以即使是卑微的我沾染上了黑暗,也不会玷污到‘那个我’的。再说了——要论渺小的躯壳,难道就真的有完全洁净的吗?”
“这就是你放弃自己、逃避道德审判的理由?”以赛亚问道。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帝人接着说道,“既然已有的道德原则对人按‘是否有罪’进行的划分最终只能将所有人划分到‘有罪’一侧,那与其在这无谓的秩序下下庸碌一生,不如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一种新的秩序——如果人生注定是痛苦的,而沉浸于梦境则被认为是懦弱的,那就喝下我的鲜血,一起来加入酒神的祭典吧:你依旧处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所触碰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以赛亚将手中的骰子狠狠摔在了地上,然后开始仰天大笑。
“有趣啊,真是太有趣了!”以赛亚说道,“这下我可真是死而无憾了,但愿你永远不会犯下那‘最终的罪过’吧。顺便一提,你的前辈——一个高估自己的傲慢的提坦神——才是最先取得绝大部分火种的,但是他并没有被绑在高加索山上,只是在脸上留下了那可怕的疤痕;不过兴许他愿意送给你些什么。”说罢,他便离开了神殿。淡黄色鬃毛的狮子急忙追赶上去,与以赛亚厮杀了起来。
与此同时,神殿内,一个穿着蓝色外套的人凭空变出了一把三叉戟,递给了帝人。少年愣了一下,随即微笑着接过了三叉戟。
“你就是普罗米修斯?”帝人问道。
“我的另一个名字叫波塞冬,或者叫撒旦也行。”那人答道。
帝人正打算接话,却被身旁那身着蓝色长袍的祭司打断了。
“不论你是海神还是恶魔,在这里,已经喝下酒神之血的你只不过是千千万万的酒神使者之一罢了。”祭司向前跨了一步。
“奥西里斯(注⑥),”波塞冬咬着牙念出了这个名字,“何时轮到你这外邦的蛮族来说话?”
“外邦又如何,蛮族又如何?”奥西里斯带着有些轻佻的语气回答道,“不管到了哪里,酒神永远是酒神,酒神是要用那疯狂的祭典为人们注定痛苦的生活带去艺术的欢愉的。”
“不过,这只是主要目的。”帝人微微低着头,喃喃自语道。
“……难道还有什么次要目的吗?”奥西里斯疑惑地问道。
“就文明人的角度来讲,既然要举行祭典,就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帝人用手指抵住了颧骨,“那么,为了避免使其变得空洞,就现实来说,救世也应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这往往意味着流血与牺牲也是必不可少的。”帝人皱了皱眉,用手指狠狠地压了一会儿颧骨,之后将掉在地上的羔羊头套又重新戴了回去。
酒神与他的使者们一起走出了神殿,外面是一幅都市中常见的车水马龙的景象——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喝过酒神的鲜血的,只是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包括了几个肮脏而丑陋的身影。酒神命令自己的使者们将这些人拦了下来,之后拖到神殿旁未被阳光照亮的阴影中殴打,直到他们将那一口酒吐出来为止。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了起来,这其中有酒神的信徒,也有被赶走了却依旧要来凑热闹的人,以及越来越多肮脏可憎的人。帝人环顾着四周,突然,他在地平线上捕捉到了一丝摇曳着的火光。少年不顾一切地向着它奔跑,可周遭的景致却变得越来越荒凉,道路变得越来越窄,跟随着他的人也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少年孤单一人的身影,一处断崖和唯一的一根看上去似乎能走人的钢丝,和眼前的那一团迷雾,以致完全看不到前方的道路。
帝人迟疑了片刻,还是走上了钢丝——他渴望看到那边的风景。他在摇晃着的钢丝上小心地前进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穿过了迷雾,走完了钢丝,站在了紧实的土地上。而此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悬崖彼端的景象却简单得令人害怕:
一座祭坛上立着一面镜子。
像是早就料到了这一景象一般,帝人一步一步登上了祭坛。可就在羔羊正打算走上最后一级阶梯的时候,他感到浑身被什么温暖的东西包裹住了,眼前也变得光明了起来。
“帝人……你这个混账。”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激动万分的帝人不禁呼唤起了自己一直思念着的挚友——不,挚爱之人的名字。
“……正臣。”
帝人感到自己就要融化在这团温暖中了,实际上依旧贪恋着这份温暖的他却咬紧了牙关,用三叉戟不顾一切地刺了出去。
骑士打扮的太阳神被刺伤了,倒在地上,却依旧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帝人的名字。
满面尘土的帝人走到镜子前,将自己的羔羊头套摘下来戴在了镜中的酒神头上,然后呜咽着说道:“正臣……对不起,可是为何……你却要让我犯下……那名为怜悯的最终罪过?”话音刚落,帝人便用三叉戟将镜子刺得粉碎,自己也从祭坛上滚落了下去,掉进了万丈深渊;正臣见状,也爬到悬崖边,跟着掉了下去。
在深渊底端那无尽的黑暗中,日神紧紧抱住了酒神,那最烈的葡萄酒在太阳的炙烤下喷涌着——在这似梦非梦、似醉非醉的混沌中,他们合为了一体。
与此同时,在远方静静观看着这一“古希腊式悲剧”的上帝被终于找到了他的淡黄色鬃毛的狮子撕成了碎片。
一切最终归于寂静。
悬崖边偶然掉落的一个火柴盒上画着的女孩目睹了这一切。她竟也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