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谢花飞飞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
落絮轻沾扑秀帘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
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 洒上空枝见血痕
愿侬此日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
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思去侬收葬 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孤独诗情
黛玉的三首歌行体长诗《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以及《桃花行》,是在《红楼梦》中大放异彩的三篇文学精品。它们不仅是曹雪芹极尽笔工的佳篇力作,篇幅之长胜过其他诗词,而且还是具有重要命运启示性的“诗谶”之作。诗谶,就是以诗为谶语,诗里预言的是人物的未来。所以这首《葬花吟》,黛玉写出的花,其实就是她。
而《葬花吟》的创作,又是这三首长诗中,作者着墨最多、用心最深的描写。这首诗甚至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黛玉一边葬花、一边泣诵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首由春光参与、由落花参与、由泪水参与、由大自然参与的天地之作,它一诞生,就不属于人间,只属于天地间。
所以,这样的佳作天成,在世间的绽放一定是十分吝惜、十分讲究缘法的。黛玉的好诗大多都有诗社姐妹们的称赞赏读,而这首《葬花吟》,由于没有落笔的记 载,它只闪耀在黛玉吟诵而过的唇齿间,随着语音落下,诗情也如那葬花一般、化入泥土,不复再现。这样疏忽而逝的惊艳之作,不肯常对人间开放。
因为上天知道,这样一首悲泣春花、悲哀命运、风流自然却不够吉利喜庆的诗章,也不是人间喜爱的调调,也不是凡人接受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文章辞藻只肯在知音的面前惊鸿一现。
“佳作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种灵性之作的知音是谁呢?显然,是宝玉。
这首诗,是孤苦愁闷的黛玉吟给自己听的,她的听众,本来只有在落寞春朝陪伴着她的自然天地。然而春天却嫌这精彩的诗篇不该湮没于花谢花飞的孤独里,于是安排了宝玉凑巧在此时路过小山坡,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这篇《葬花吟》。
宝玉不愧是黛玉的知己、是大自然的知己,他被这婉转伤怀的诗句深深打动,不觉痴倒。他懂黛玉,他懂葬花的行为和葬花诗里的情怀,他怜惜这个女孩儿独自一人诉说无处的忧伤。如果说,黛玉是花草的守护者,那么宝玉,就正是黛玉的守护者。
黛玉前世本是一棵绛珠草,所以她对花草格外有一份敏锐的感知和独特的理解。因此,虽然大观园诗社里众人歌咏的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等诗作都各有高妙,但只有黛玉的诗,写出的是海棠的香魂,问倒的是菊花的心事,叹破的是柳絮韶华白头、飘摇一生的悲凉。她关注的永远是这些花草热闹背后的孤独。就像她自己,热闹和孤独在她身上矛盾又激烈地冲突着,她能在欢宴时体会到人群中的孤独,又能在孤独时得到一个人的精神狂欢。
众人都赏花,唯有黛玉葬花,她看过了花绽放在人前的笑脸,更要听花在人背后的哭诉。见花惜泪,黛玉才是真正的惜花人。她并非将花木看作是赏玩的对象,她是在用惺惺相惜之心,看待一场生命的悲喜。
她用葬花,隆重为花的生命礼赞。
之所以她会频频对花伤怀,是因为她在花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样的花开寂寞、孤芳自赏,一样地飘摇无主、易被雨打风吹去,一样地好景不常在、预感着红颜薄命的结局。
花,历来都只有美人才能用之作比,杨贵妃被称作有“羞花”之貌,是借助了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那是夸张的溢美之词。而其他女子,谁敢毫不自谦地以花来自喻芳姿呢!就像宋词里问的:“花强妾貌强?”这从来都是女子心底最怕的问题,最怕花比人娇。
而黛玉却敢以花自比,而且一比再比。其实,这是她在常常展露的自卑自伤背后,更有一种高于旁人的自傲。
傲不可侵,是内在的风骨;傲不示人,是外在的修养。黛玉不与人说的伤感与骄傲,是她的一种文化贵族心态。
这种心态,很多人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早已丧失了那样的风骨培养。今天我们如果再去路边葬花,一定会受到嘲讽,因为那种贵族品位的文化理解没有被传承下来。我们身边,太少黛玉和宝玉那样能够撷取自然之美、能够关注细微情怀的人。
再者,离开了大观园这样生活无忧、诗情画意的理想园,也不容易再找到适合诗意从容生发的土壤了。今天我们生活的土壤,都只为迅速结果而存在,几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在埋藏梦幻上。我们的步履太过匆匆,我们的灵魂太过焦虑,我们的思维太过单向,我们的心态太过急切,所以,我们把最初的梦都丢了,做梦、怀梦、朝着梦的方向出发,那似乎只能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天方夜谭。
但是,这种苍白无梦的状态,并不简单是因为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而更多是因为我们生活态度的粗陋。
黛玉之所以会是大观园里唯一肯赏花、更能葬花的人,也是因为她的出身和贾府中人不一样。她的父亲是前朝探花,因此她是知识分子诗书传家的子女,而非贾府 子弟乃是靠开国之功而迅速崛起的武官之后。文化世家的熏陶,使黛玉的品位和认知与众不同,这一点,在林妹妹初进荣国府的第一顿晚餐上就表露无遗:黛玉家并 不在饭后立即用茶,深谙涵养生息之法;而贾府的生活方式虽富足,却少了一些书香门第的家传教养,少了一些真正讲究的品位和文化浸润的积累。所以黛玉的矛盾 就在于,既寄人篱下,又高人一筹。
此身不得不委曲求全,而此心又生在高处不胜寒。
见花惜泪,是因为那芳菲柔弱似人;以花自比,又是因为黛玉自视甚高。读花解花、怜花葬花,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源于她内心细腻的触感与矜持的孤独。
而孤独,又正是因为在她的精神深处,常常与旁人无法对话。
二、美学范式
黛玉的孤独,是因为她已经超越了大众审美的层面。黛玉是诗的化身、美的化身,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她作诗出色、资容出众,而是她所具有的诗心,构成了一种含蓄的、甚至近乎病态的行为美学。而这种审美形态,正符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美的几近严苛的追求。
看黛玉葬花之前,“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此时她的形象是“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活脱脱一幅田园闲居的妆点,却又比真正的农人多了精致和讲究。她这样的造型正是从陶渊明田园诗“带月荷锄归”的意象中化出来的。
这样亲近自然、远离尘俗的出世情怀,是仕人阶层共有的精神向往,陶渊明耕出的是中国仕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心灵向往,无奈往往都只能藏在心灵,不得实现。而黛玉出神入化地将这种田园之乐的行为女性化、唯美化、诗意化,令自然不仅在远山,也在身边,对自然不仅是羡慕,也是融入。人与自然,真正发生了对话。
如果说曹植辞藻华丽的《洛神赋》是写出了水边女子的最佳典范,那么曹雪芹几笔勾勒的黛玉葬花,就是打造出了大地女儿的最美范式。一个是洛神,一个如花神。
黛玉正像是花神,她在一片香海中,关怀着生命的坠落。通过一次葬花,人之于自然,不再只是路过,而是深刻的参与。
除了在葬花之前“带月荷锄归”的意象,黛玉于葬花之后的歌咏神伤,还演绎出了古诗里另一出美的脚本,就是晏几道词里写过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那样有风吹过的寂寞,那样花也零落的孤独。中国诗人认为,浅薄的轻快是不值得依依落笔、细细把赏的。所以中国诗词里,往往都在描写一种个体的“闲愁”,那 是怀有心事的一种寂寥,是含蓄甚至略带偏执的美。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个体,在本质上都是孤独,所以大家总是在不由自主地追求热闹与欢笑,就是为了避免和摆脱这种个体上的孤独。但是频繁无谓地追求笑闹,绝 对不是处理孤独的好方法,它会让人越来越不敢面对独自一人的寂寥,会让人的内心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对外界产生依赖。而我们古代的知识阶层,就会时不时地品 味和享受一下这种孤独,为自己的生命故意地留白。
生命里有一种孤独,是不允许被打扰的。
孤独本身,就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就像黛玉在花冢旁、在繁树下,痴痴念着句子的哀思,正是对生命孤独的处理和升华。即使当时的她,是那样伤怀,但这伤怀在残花落红的包围中,也美得格外触目惊心!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也在于它推出了一系列美的形象、美的范式。湘云的醉眠芍药是美、宝琴的雪映红梅是美、晴雯的病补雀裘是美、龄官的花下划 蔷是美……而黛玉葬花,在曹雪芹造就的各种美里首屈一指,就如同《葬花吟》在曹雪芹的诗文创作中尤为不朽。黛玉葬花,是把文化推向了一种细腻精致的巅峰, 为审美赋予了一种哲思上的人文关注。
黛玉葬花,本是她通过花来自怜身世的艰难处境、自悲命运的凄凉走向。然而就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黛玉反而用她的美丽与哀愁,用她在大地上洒落的泪水与诗情,为文学、为美学、为人间,留下了一份不输于洛水女神的审美典范。
三、务虚精神
黛玉这种超凡脱俗的美,让宝玉在山坡上听得“不觉痴倒”。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活色生香的美,也曾让宝玉看得发呆忘情,那就是宝钗身上的魅力。
《红楼梦》在章节设置上、在人物刻画上,永远都在构架一种相对的平衡,让读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比如黛玉泣颂《葬花吟》的这一回中,就对应地写到了“宝钗扑蝶”的情节:宝钗,带来了另一种美的形式。
在同一日的春色里,黛玉葬花,宝钗却扑追一双玉色蝴蝶,举着小扇一路穿花度柳,香汗淋漓,娇喘细细。作者是有意将宝钗的美与黛玉的美在同一回目里作对比,用一个动态美、一个静态美,关照着两种不同的生命。
宝钗扑蝶,是追求活的价值;黛玉葬花,是叩问死的意义。我们不妨形象地将她们两人比喻为一个是经济家,一个是哲学家:
宝钗重入世,黛玉重出世;
宝钗要在热闹中实现人生价值,黛玉是在孤独里提升生命品质;
宝钗努力抓取眼前的利益,她看重的是现在,黛玉用心了悟终极的目的,她思考的是未来;
宝钗想要捉住蝴蝶,她关心的是迎入和获得,黛玉要为花瓣善后,她关注的是送别和失去。
在美学形象上:
宝钗如一朵春天的鲜花,开在世间,寻求认可与赞赏;黛玉如一片秋天的红叶,走向自然,独自美丽与沉思。
在价值观念上:
宝钗务实,黛玉务虚。也许这是因为她们两人,一个尘缘甚深,一个仙缘未了。
在美的领域里没有高下之分,不只宝钗与黛玉两人,甚至妙玉论茶、甚至平儿理妆、甚至凤姐弄权、甚至可卿悬梁……也都各有其美。红颜白骨,俱是你我。大千世界,有心即有美。
但从精神境界上来讲,黛玉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诉求。人类只有超越了自然性的行为、而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来主动地反思自身的存在意义、存在形式,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实现了文化自觉的人。
但尘世中过于务实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因为这些发乎灵魂的体悟和感触,并不能为现世带来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然而,宝玉却懂得黛玉的一切。前世,神瑛侍者的甘露滋养着绛珠仙草生命的存活,今生,黛玉的诗情滋养着宝玉心灵牧场的丰盛。彼此懂得,是为知己。
务虚,有时候是一种高贵,是足够丰富的心灵才能支撑出的一片精神世界。
四、灵魂归宿
黛玉葬花,连一片片花瓣都用情至深,看似黛玉的心无孔不入、看似黛玉的情无处不在,但其实,黛玉并不是多情的人。她和宝玉不同,脂砚斋在评本里透露出曹 雪芹曾为红楼人物写过情榜,情榜上宝玉是天性能够“情不情”的人,也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情有意,他都甘心为之付出情感,以有情待无情;而黛玉的本性 是“情情”的人,她只为那些对她有情有感的人和事用情,她只肯以有情待有情。黛玉原本就不如宝玉的生命力旺盛充沛,所以她没有多余的热情贡献给世间,她全部的感情,一半用来爱宝玉,一半用来伤自己。
葬花吟诗,看似美绝,其实那正是她在孤苦无依、百般无奈之下,一种抒发伤心事又反被伤心事所伤的行为,如同“举杯消愁愁更愁”,黛玉写诗,更伤自己。
而黛玉以血泪写就的这首《葬花吟》带给读者的感受,正如《西厢记》带给黛玉的感受,那是一种“辞藻警人,馀香满口”的惊艳。除了字句之美,诗中的感情基 调也极为震撼人
落絮轻沾扑秀帘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
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 洒上空枝见血痕
愿侬此日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
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思去侬收葬 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一、孤独诗情
黛玉的三首歌行体长诗《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以及《桃花行》,是在《红楼梦》中大放异彩的三篇文学精品。它们不仅是曹雪芹极尽笔工的佳篇力作,篇幅之长胜过其他诗词,而且还是具有重要命运启示性的“诗谶”之作。诗谶,就是以诗为谶语,诗里预言的是人物的未来。所以这首《葬花吟》,黛玉写出的花,其实就是她。
而《葬花吟》的创作,又是这三首长诗中,作者着墨最多、用心最深的描写。这首诗甚至不是写出来的,而是黛玉一边葬花、一边泣诵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首由春光参与、由落花参与、由泪水参与、由大自然参与的天地之作,它一诞生,就不属于人间,只属于天地间。
所以,这样的佳作天成,在世间的绽放一定是十分吝惜、十分讲究缘法的。黛玉的好诗大多都有诗社姐妹们的称赞赏读,而这首《葬花吟》,由于没有落笔的记 载,它只闪耀在黛玉吟诵而过的唇齿间,随着语音落下,诗情也如那葬花一般、化入泥土,不复再现。这样疏忽而逝的惊艳之作,不肯常对人间开放。
因为上天知道,这样一首悲泣春花、悲哀命运、风流自然却不够吉利喜庆的诗章,也不是人间喜爱的调调,也不是凡人接受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文章辞藻只肯在知音的面前惊鸿一现。
“佳作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种灵性之作的知音是谁呢?显然,是宝玉。
这首诗,是孤苦愁闷的黛玉吟给自己听的,她的听众,本来只有在落寞春朝陪伴着她的自然天地。然而春天却嫌这精彩的诗篇不该湮没于花谢花飞的孤独里,于是安排了宝玉凑巧在此时路过小山坡,一字不落地听到了这篇《葬花吟》。
宝玉不愧是黛玉的知己、是大自然的知己,他被这婉转伤怀的诗句深深打动,不觉痴倒。他懂黛玉,他懂葬花的行为和葬花诗里的情怀,他怜惜这个女孩儿独自一人诉说无处的忧伤。如果说,黛玉是花草的守护者,那么宝玉,就正是黛玉的守护者。
黛玉前世本是一棵绛珠草,所以她对花草格外有一份敏锐的感知和独特的理解。因此,虽然大观园诗社里众人歌咏的海棠诗、菊花诗、柳絮词等诗作都各有高妙,但只有黛玉的诗,写出的是海棠的香魂,问倒的是菊花的心事,叹破的是柳絮韶华白头、飘摇一生的悲凉。她关注的永远是这些花草热闹背后的孤独。就像她自己,热闹和孤独在她身上矛盾又激烈地冲突着,她能在欢宴时体会到人群中的孤独,又能在孤独时得到一个人的精神狂欢。
众人都赏花,唯有黛玉葬花,她看过了花绽放在人前的笑脸,更要听花在人背后的哭诉。见花惜泪,黛玉才是真正的惜花人。她并非将花木看作是赏玩的对象,她是在用惺惺相惜之心,看待一场生命的悲喜。
她用葬花,隆重为花的生命礼赞。
之所以她会频频对花伤怀,是因为她在花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样的花开寂寞、孤芳自赏,一样地飘摇无主、易被雨打风吹去,一样地好景不常在、预感着红颜薄命的结局。
花,历来都只有美人才能用之作比,杨贵妃被称作有“羞花”之貌,是借助了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那是夸张的溢美之词。而其他女子,谁敢毫不自谦地以花来自喻芳姿呢!就像宋词里问的:“花强妾貌强?”这从来都是女子心底最怕的问题,最怕花比人娇。
而黛玉却敢以花自比,而且一比再比。其实,这是她在常常展露的自卑自伤背后,更有一种高于旁人的自傲。
傲不可侵,是内在的风骨;傲不示人,是外在的修养。黛玉不与人说的伤感与骄傲,是她的一种文化贵族心态。
这种心态,很多人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早已丧失了那样的风骨培养。今天我们如果再去路边葬花,一定会受到嘲讽,因为那种贵族品位的文化理解没有被传承下来。我们身边,太少黛玉和宝玉那样能够撷取自然之美、能够关注细微情怀的人。
再者,离开了大观园这样生活无忧、诗情画意的理想园,也不容易再找到适合诗意从容生发的土壤了。今天我们生活的土壤,都只为迅速结果而存在,几乎没有一寸土地可以浪费在埋藏梦幻上。我们的步履太过匆匆,我们的灵魂太过焦虑,我们的思维太过单向,我们的心态太过急切,所以,我们把最初的梦都丢了,做梦、怀梦、朝着梦的方向出发,那似乎只能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天方夜谭。
但是,这种苍白无梦的状态,并不简单是因为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而更多是因为我们生活态度的粗陋。
黛玉之所以会是大观园里唯一肯赏花、更能葬花的人,也是因为她的出身和贾府中人不一样。她的父亲是前朝探花,因此她是知识分子诗书传家的子女,而非贾府 子弟乃是靠开国之功而迅速崛起的武官之后。文化世家的熏陶,使黛玉的品位和认知与众不同,这一点,在林妹妹初进荣国府的第一顿晚餐上就表露无遗:黛玉家并 不在饭后立即用茶,深谙涵养生息之法;而贾府的生活方式虽富足,却少了一些书香门第的家传教养,少了一些真正讲究的品位和文化浸润的积累。所以黛玉的矛盾 就在于,既寄人篱下,又高人一筹。
此身不得不委曲求全,而此心又生在高处不胜寒。
见花惜泪,是因为那芳菲柔弱似人;以花自比,又是因为黛玉自视甚高。读花解花、怜花葬花,所有这些行为,都是源于她内心细腻的触感与矜持的孤独。
而孤独,又正是因为在她的精神深处,常常与旁人无法对话。
二、美学范式
黛玉的孤独,是因为她已经超越了大众审美的层面。黛玉是诗的化身、美的化身,这绝不仅仅是由于她作诗出色、资容出众,而是她所具有的诗心,构成了一种含蓄的、甚至近乎病态的行为美学。而这种审美形态,正符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美的几近严苛的追求。
看黛玉葬花之前,“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此时她的形象是“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帚”,活脱脱一幅田园闲居的妆点,却又比真正的农人多了精致和讲究。她这样的造型正是从陶渊明田园诗“带月荷锄归”的意象中化出来的。
这样亲近自然、远离尘俗的出世情怀,是仕人阶层共有的精神向往,陶渊明耕出的是中国仕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心灵向往,无奈往往都只能藏在心灵,不得实现。而黛玉出神入化地将这种田园之乐的行为女性化、唯美化、诗意化,令自然不仅在远山,也在身边,对自然不仅是羡慕,也是融入。人与自然,真正发生了对话。
如果说曹植辞藻华丽的《洛神赋》是写出了水边女子的最佳典范,那么曹雪芹几笔勾勒的黛玉葬花,就是打造出了大地女儿的最美范式。一个是洛神,一个如花神。
黛玉正像是花神,她在一片香海中,关怀着生命的坠落。通过一次葬花,人之于自然,不再只是路过,而是深刻的参与。
除了在葬花之前“带月荷锄归”的意象,黛玉于葬花之后的歌咏神伤,还演绎出了古诗里另一出美的脚本,就是晏几道词里写过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那样有风吹过的寂寞,那样花也零落的孤独。中国诗人认为,浅薄的轻快是不值得依依落笔、细细把赏的。所以中国诗词里,往往都在描写一种个体的“闲愁”,那 是怀有心事的一种寂寥,是含蓄甚至略带偏执的美。
其实每个人的生命个体,在本质上都是孤独,所以大家总是在不由自主地追求热闹与欢笑,就是为了避免和摆脱这种个体上的孤独。但是频繁无谓地追求笑闹,绝 对不是处理孤独的好方法,它会让人越来越不敢面对独自一人的寂寥,会让人的内心越来越空虚、越来越对外界产生依赖。而我们古代的知识阶层,就会时不时地品 味和享受一下这种孤独,为自己的生命故意地留白。
生命里有一种孤独,是不允许被打扰的。
孤独本身,就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就像黛玉在花冢旁、在繁树下,痴痴念着句子的哀思,正是对生命孤独的处理和升华。即使当时的她,是那样伤怀,但这伤怀在残花落红的包围中,也美得格外触目惊心!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也在于它推出了一系列美的形象、美的范式。湘云的醉眠芍药是美、宝琴的雪映红梅是美、晴雯的病补雀裘是美、龄官的花下划 蔷是美……而黛玉葬花,在曹雪芹造就的各种美里首屈一指,就如同《葬花吟》在曹雪芹的诗文创作中尤为不朽。黛玉葬花,是把文化推向了一种细腻精致的巅峰, 为审美赋予了一种哲思上的人文关注。
黛玉葬花,本是她通过花来自怜身世的艰难处境、自悲命运的凄凉走向。然而就像“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黛玉反而用她的美丽与哀愁,用她在大地上洒落的泪水与诗情,为文学、为美学、为人间,留下了一份不输于洛水女神的审美典范。
三、务虚精神
黛玉这种超凡脱俗的美,让宝玉在山坡上听得“不觉痴倒”。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活色生香的美,也曾让宝玉看得发呆忘情,那就是宝钗身上的魅力。
《红楼梦》在章节设置上、在人物刻画上,永远都在构架一种相对的平衡,让读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比如黛玉泣颂《葬花吟》的这一回中,就对应地写到了“宝钗扑蝶”的情节:宝钗,带来了另一种美的形式。
在同一日的春色里,黛玉葬花,宝钗却扑追一双玉色蝴蝶,举着小扇一路穿花度柳,香汗淋漓,娇喘细细。作者是有意将宝钗的美与黛玉的美在同一回目里作对比,用一个动态美、一个静态美,关照着两种不同的生命。
宝钗扑蝶,是追求活的价值;黛玉葬花,是叩问死的意义。我们不妨形象地将她们两人比喻为一个是经济家,一个是哲学家:
宝钗重入世,黛玉重出世;
宝钗要在热闹中实现人生价值,黛玉是在孤独里提升生命品质;
宝钗努力抓取眼前的利益,她看重的是现在,黛玉用心了悟终极的目的,她思考的是未来;
宝钗想要捉住蝴蝶,她关心的是迎入和获得,黛玉要为花瓣善后,她关注的是送别和失去。
在美学形象上:
宝钗如一朵春天的鲜花,开在世间,寻求认可与赞赏;黛玉如一片秋天的红叶,走向自然,独自美丽与沉思。
在价值观念上:
宝钗务实,黛玉务虚。也许这是因为她们两人,一个尘缘甚深,一个仙缘未了。
在美的领域里没有高下之分,不只宝钗与黛玉两人,甚至妙玉论茶、甚至平儿理妆、甚至凤姐弄权、甚至可卿悬梁……也都各有其美。红颜白骨,俱是你我。大千世界,有心即有美。
但从精神境界上来讲,黛玉的生命形态呈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诉求。人类只有超越了自然性的行为、而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来主动地反思自身的存在意义、存在形式,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实现了文化自觉的人。
但尘世中过于务实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因为这些发乎灵魂的体悟和感触,并不能为现世带来多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然而,宝玉却懂得黛玉的一切。前世,神瑛侍者的甘露滋养着绛珠仙草生命的存活,今生,黛玉的诗情滋养着宝玉心灵牧场的丰盛。彼此懂得,是为知己。
务虚,有时候是一种高贵,是足够丰富的心灵才能支撑出的一片精神世界。
四、灵魂归宿
黛玉葬花,连一片片花瓣都用情至深,看似黛玉的心无孔不入、看似黛玉的情无处不在,但其实,黛玉并不是多情的人。她和宝玉不同,脂砚斋在评本里透露出曹 雪芹曾为红楼人物写过情榜,情榜上宝玉是天性能够“情不情”的人,也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对自己有情有意,他都甘心为之付出情感,以有情待无情;而黛玉的本性 是“情情”的人,她只为那些对她有情有感的人和事用情,她只肯以有情待有情。黛玉原本就不如宝玉的生命力旺盛充沛,所以她没有多余的热情贡献给世间,她全部的感情,一半用来爱宝玉,一半用来伤自己。
葬花吟诗,看似美绝,其实那正是她在孤苦无依、百般无奈之下,一种抒发伤心事又反被伤心事所伤的行为,如同“举杯消愁愁更愁”,黛玉写诗,更伤自己。
而黛玉以血泪写就的这首《葬花吟》带给读者的感受,正如《西厢记》带给黛玉的感受,那是一种“辞藻警人,馀香满口”的惊艳。除了字句之美,诗中的感情基 调也极为震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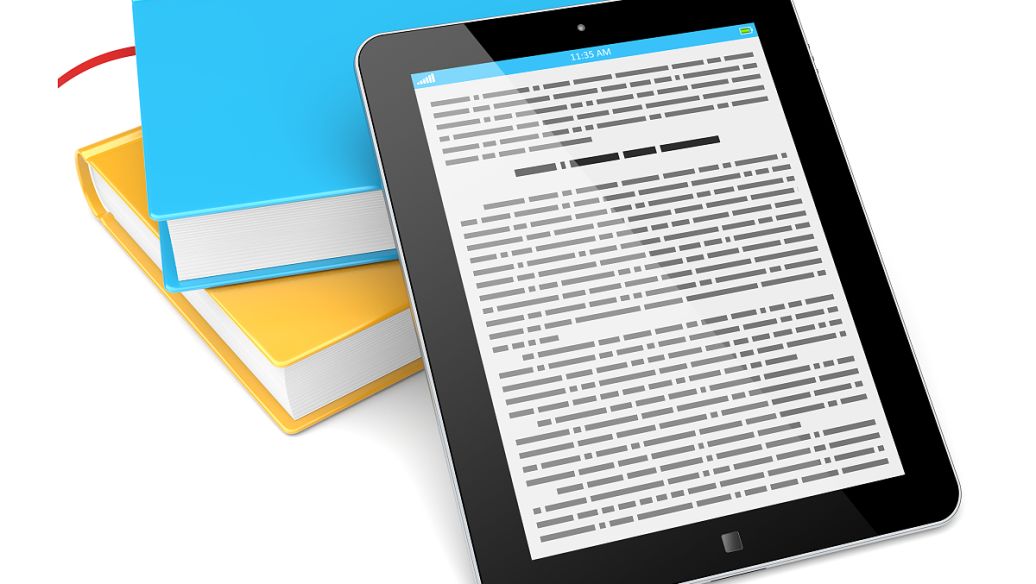



 九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