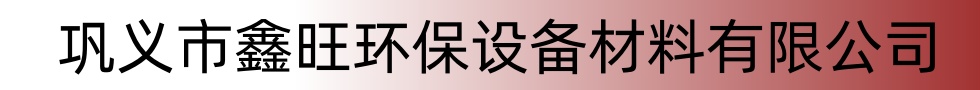阿父总是来去匆匆,我数着院子里树枝上稀疏的叶子,今日掉一片,明日掉一片,日日数、夜夜数,掉干净了就近年关,阿父顶着风,胡同口买来的糖葫芦上应该沾着雪,踏进院子里时像在叫小鸟:“获姐儿——获姐儿——”。
⠀
但我要同他说我不能吃糖,要给他瞧我刚掉下来的牙,王阿嬷说,我在长大。
⠀
可我没有等到父亲,来了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阿父同他一样高,春天里能将我架在肩上去摘树上的花。他披着的一身寒气像被子一样厚,蹲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眼睛,突然就变红了,像我掉牙一样快。
⠀
于是我问他:“你是谁?你怎么这么难过。”
⠀
我听到婶婶尖厉的哭声,也不是很像哭声,我没有听到眼泪。
⠀
她扑过来同我说些什么死呀、苦啊,我稍稍往后躲避开她枯瘦又硌人的手。婶婶其实很少来我这边,院子不大只有一点距离,但每次都是叔叔过来。她可能并不喜欢我,但这没什么紧要的,阿父喜欢我就足够了。每次婶婶来的时候,都是阿父回家的日子,于是我踮起脚尖想要越过男子的肩头往外看,看看阿父在哪里。
⠀
我还是被婶婶抓住了,像一只鸟一样攥在手里。她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痛,囫囵来囫囵去都是一句:我苦命的获姐儿以后可怎么办啊——,我实在不理解,想要挣脱她,像枝头飞走的喜鹊一样。
⠀
我在婶婶怀里艰难地转过头看向那个男子,脸颊憋得通红,用着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到的声音问着:“你是谁?你认识我阿父吗?他去哪里了?”
枝头最后一片树叶就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掉了下来,我突然想到。
要过年了。
⠀
但我要同他说我不能吃糖,要给他瞧我刚掉下来的牙,王阿嬷说,我在长大。
⠀
可我没有等到父亲,来了一位身形高大的男子,阿父同他一样高,春天里能将我架在肩上去摘树上的花。他披着的一身寒气像被子一样厚,蹲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眼睛,突然就变红了,像我掉牙一样快。
⠀
于是我问他:“你是谁?你怎么这么难过。”
⠀
我听到婶婶尖厉的哭声,也不是很像哭声,我没有听到眼泪。
⠀
她扑过来同我说些什么死呀、苦啊,我稍稍往后躲避开她枯瘦又硌人的手。婶婶其实很少来我这边,院子不大只有一点距离,但每次都是叔叔过来。她可能并不喜欢我,但这没什么紧要的,阿父喜欢我就足够了。每次婶婶来的时候,都是阿父回家的日子,于是我踮起脚尖想要越过男子的肩头往外看,看看阿父在哪里。
⠀
我还是被婶婶抓住了,像一只鸟一样攥在手里。她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痛,囫囵来囫囵去都是一句:我苦命的获姐儿以后可怎么办啊——,我实在不理解,想要挣脱她,像枝头飞走的喜鹊一样。
⠀
我在婶婶怀里艰难地转过头看向那个男子,脸颊憋得通红,用着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到的声音问着:“你是谁?你认识我阿父吗?他去哪里了?”
枝头最后一片树叶就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掉了下来,我突然想到。
要过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