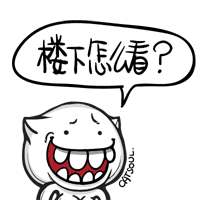衙下中学吧 关注:113贴子:4,628
二
神教,扎根于西部高原,作为多神信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成分是多种宗教溶合的产物。
首先,它受过苯教和佛教的影响:
早在原始部落联盟的时期,雪域高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宗教——苯教(初为象雄国国教)。费尔巴哈说:“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的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宗教的本质》),苯教的自然崇拜的色彩很浓烈,认为万物有灵,它崇尚天上、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尤重山神和水神。重祭祀、跳神、占卜、禳解等。藏族的先民所面临的是喜怒无常的高原,有时刮风,有时暴雪不断,它的强大使先民在它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为了调解与自然的矛盾,就把大自然加以人格化,觉得到处都充满灵气,从而用祈禳等各种方式求得想象中的神灵保护。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后,于公元七世纪中叶挫败苯教,成为藏民族的理论武器,指导和规范藏人的行为,还有宇宙观、生死观和价值观。(才让《青藏高原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佛教在藏民的传播中,也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祭祀仪式,接受了苯教对现实世界的众多解释,岁月把它捏塑成以佛教教义为核心,以苯教仪规为外壳的藏传佛教。
临洮南部、康乐、渭原的会川镇、临潭、岷县、和政一带,过去是藏民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现在这一带群众过的藏风浓郁的“拉扎节”(祭山神的活动),及过去临洮五月端阳迎接八位官神(龙王,即水神)的祭典活动,不是由僧、道主持,而是师公跳神。祭山祭水,很显然这是苯教自然崇拜的遗传。而跳神演唱的诸神,包括玉皇大帝、天庭诸神、还有忠臣良将、达子神、菩萨娘娘等,及神教的十二护神(骡子天王、犀牛带海、六臂护神、维托护神等)绝大多数为藏传佛教的神祗,看来它受苯教和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次,神教也受过萨满教的影响:
萨满教是蒙族、满族及一些少数民族流行中亚一带的原始宗教,也是一种古老的多神崇拜宗教。萨满一词的意思是“处于兴奋状态的人,被神附体的人”,“激动不安疯狂乱舞的人”。萨满教成熟于母系社会的繁荣期,是史前产物,有大量母系氏族残余,以女神崇拜为主体。萨满中女性居多,男性萨满也必须学女人的腔调动作,这是和神教不同的地方。萨满教对世界上、中、下三界的划分与神教相同;跳神的程序:请神、隆神、神附体、述神言、送神归等基本相同;跳神穿衣裙、击神鼓、系鹿铃、跳舞步,基本相似;前面提到的“达子神”,可能就是萨满教的神祗。随着元朝的统治,萨满教波及甚广。直至十六世纪下半叶,黄教进入蒙古社会,取而代之,萨满教才基本结束。神教与萨满教有许多特征,是相似的。
第三,道教与神教的关系也很微妙:
道教是汉民族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它和神教一样,渊源于古代的巫术。道教道士信奉道教经典、规戒,熟悉各种斋醮祭祷仪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作全真、正一两大教派。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信奉正一派的道士不出家(也有出家的),俗称“俗家道士”,即阴阳生。这一派主要从事“堪舆”,看阳宅、风水、圆光避邪、书符、合婚、算卦等,道教也是多神信仰,好用符篆咒语趋福避祸,设立道场诵经,与神教大体相同。
此外,神教也受儒教影响,儒教的人物也进入神教的神谱,也以某些儒教的伦理道德作为唱诵的内容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教是一个兼收并蓄,杂揉混合的民间信仰形式,因而能为各阶层、各宗教的人们所接受,具有普泛性。就民族来说,又是汉藏合壁的,而藏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体现了高原地域文化的特色。
民俗,指民间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习惯性行为模式。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述,由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习惯谓之风,由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习尚谓之俗。正如有人说的:民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为循环运行的文化时钟。它使万物有了节律,使生活有了呼吸,使道德有了刻度,使神灵有了秩序,使人生有了轮回。有些民俗就是从宗教仪式演变过来的。有人甚至认为“民俗是退化了的宗教”。(覃光广《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就目前一般社会,婚丧仪式、选择用相避相、贴对联、送火、民间禁忌等,细细根究起来,都能找到宗教仪式的根源;民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
神教产生并兴盛于西部高原(波及云贵高原),在其祈福禳灾,敬神驱鬼的道场跳神活动中,无疑渗透着历史上承袭下来的鬼神观念和迷信色彩,透露出诸多远古生活的信息。但社会毕竟在不断发展,从古代的巫术到现代的宗教,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崇拜到精灵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由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的缓慢过程。由对自然的敬畏,到人的力量的自我肯定。由娱神逐渐向娱人方面转变。宗教是在人们无法避免、也无法改变的苦难中产生的,是人类面对苦难的心灵叹息;当然也会随着种种苦难的消除及心理问题的解决而消亡。宗教是人们的心理恐惧、心灵慰籍的表达。我们考查跳神活动,除了了解其中的愚昧迷信的内容外,还能发现其在文化和民俗方面的价值。
神教,扎根于西部高原,作为多神信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其他宗教的成分是多种宗教溶合的产物。
首先,它受过苯教和佛教的影响:
早在原始部落联盟的时期,雪域高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宗教——苯教(初为象雄国国教)。费尔巴哈说:“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这一点是一切的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宗教的本质》),苯教的自然崇拜的色彩很浓烈,认为万物有灵,它崇尚天上、山林、水泽的神鬼精灵和自然物,尤重山神和水神。重祭祀、跳神、占卜、禳解等。藏族的先民所面临的是喜怒无常的高原,有时刮风,有时暴雪不断,它的强大使先民在它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为了调解与自然的矛盾,就把大自然加以人格化,觉得到处都充满灵气,从而用祈禳等各种方式求得想象中的神灵保护。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后,于公元七世纪中叶挫败苯教,成为藏民族的理论武器,指导和规范藏人的行为,还有宇宙观、生死观和价值观。(才让《青藏高原对藏族社会的影响》)
佛教在藏民的传播中,也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祭祀仪式,接受了苯教对现实世界的众多解释,岁月把它捏塑成以佛教教义为核心,以苯教仪规为外壳的藏传佛教。
临洮南部、康乐、渭原的会川镇、临潭、岷县、和政一带,过去是藏民居住最集中的地区,现在这一带群众过的藏风浓郁的“拉扎节”(祭山神的活动),及过去临洮五月端阳迎接八位官神(龙王,即水神)的祭典活动,不是由僧、道主持,而是师公跳神。祭山祭水,很显然这是苯教自然崇拜的遗传。而跳神演唱的诸神,包括玉皇大帝、天庭诸神、还有忠臣良将、达子神、菩萨娘娘等,及神教的十二护神(骡子天王、犀牛带海、六臂护神、维托护神等)绝大多数为藏传佛教的神祗,看来它受苯教和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次,神教也受过萨满教的影响:
萨满教是蒙族、满族及一些少数民族流行中亚一带的原始宗教,也是一种古老的多神崇拜宗教。萨满一词的意思是“处于兴奋状态的人,被神附体的人”,“激动不安疯狂乱舞的人”。萨满教成熟于母系社会的繁荣期,是史前产物,有大量母系氏族残余,以女神崇拜为主体。萨满中女性居多,男性萨满也必须学女人的腔调动作,这是和神教不同的地方。萨满教对世界上、中、下三界的划分与神教相同;跳神的程序:请神、隆神、神附体、述神言、送神归等基本相同;跳神穿衣裙、击神鼓、系鹿铃、跳舞步,基本相似;前面提到的“达子神”,可能就是萨满教的神祗。随着元朝的统治,萨满教波及甚广。直至十六世纪下半叶,黄教进入蒙古社会,取而代之,萨满教才基本结束。神教与萨满教有许多特征,是相似的。
第三,道教与神教的关系也很微妙:
道教是汉民族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它和神教一样,渊源于古代的巫术。道教道士信奉道教经典、规戒,熟悉各种斋醮祭祷仪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作全真、正一两大教派。信奉全真派的道士必须出家,信奉正一派的道士不出家(也有出家的),俗称“俗家道士”,即阴阳生。这一派主要从事“堪舆”,看阳宅、风水、圆光避邪、书符、合婚、算卦等,道教也是多神信仰,好用符篆咒语趋福避祸,设立道场诵经,与神教大体相同。
此外,神教也受儒教影响,儒教的人物也进入神教的神谱,也以某些儒教的伦理道德作为唱诵的内容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教是一个兼收并蓄,杂揉混合的民间信仰形式,因而能为各阶层、各宗教的人们所接受,具有普泛性。就民族来说,又是汉藏合壁的,而藏民族民俗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体现了高原地域文化的特色。
民俗,指民间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习惯性行为模式。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述,由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习惯谓之风,由社会环境而形成的习尚谓之俗。正如有人说的:民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为循环运行的文化时钟。它使万物有了节律,使生活有了呼吸,使道德有了刻度,使神灵有了秩序,使人生有了轮回。有些民俗就是从宗教仪式演变过来的。有人甚至认为“民俗是退化了的宗教”。(覃光广《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就目前一般社会,婚丧仪式、选择用相避相、贴对联、送火、民间禁忌等,细细根究起来,都能找到宗教仪式的根源;民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
神教产生并兴盛于西部高原(波及云贵高原),在其祈福禳灾,敬神驱鬼的道场跳神活动中,无疑渗透着历史上承袭下来的鬼神观念和迷信色彩,透露出诸多远古生活的信息。但社会毕竟在不断发展,从古代的巫术到现代的宗教,经历了一个由自然崇拜到精灵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由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的缓慢过程。由对自然的敬畏,到人的力量的自我肯定。由娱神逐渐向娱人方面转变。宗教是在人们无法避免、也无法改变的苦难中产生的,是人类面对苦难的心灵叹息;当然也会随着种种苦难的消除及心理问题的解决而消亡。宗教是人们的心理恐惧、心灵慰籍的表达。我们考查跳神活动,除了了解其中的愚昧迷信的内容外,还能发现其在文化和民俗方面的价值。
正如马克思说的:“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也就是说对于迷信加以科学的解释。
在历史文献中,我们还未找到有关神教的更为详细的资料,它的发展脉络和仪式,还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仅靠我们接触看到的和采访得来的材料,毕竟带有某种局限性,而且,跳神活动随着时代也处在变异中。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师公跳神的祭祀活动,则展现的是一些丰收图,民俗风情的面画。
清代康、雍间吴之挺《竹枝词》第五首写的迎神赛会的情况是:
五月清明作道场,村村迓鼓拜龙王。
巫阳抢得灵湫至,一路甘霖作麦香。
明末清初临洮诗人张晋写的《迎神曲》,显得更为详尽具体:
桃花吹风杏花雨,山口春入古庙宇。
石炉突突香烟举,吹竽撞钟纷歌舞。
巫娘婆娑唱神来,土壁龙蛇眼欲开。
纸钱绕红飞蝶灰,精灵和乐不能回。
初祝螟虫化为水,大家再祝旱魃死。
殷勤拜跪三祝己,田熟牛肥疾病止。
献神羊猪酬神酒,送神神归神保佑。
白马金袍神康寿,年年与我好麦豆。
师公跳神中,迎接水神龙王,是一个大关节,是它的主要活动。我在《临洮端午迎接八位官神赛会风俗的调查》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从略。不过官神人数各地不相统一,衙下集寺洼庙会有十二位,临潭、岷县有十八位,还多了几位女性。各地都有自己的风情特色。
综上所述,在高原这一独特环境下,孕育产生的扇鼓傩舞仪式,它历史久远,受多种宗教的影响,形式独特,具有原始性、祭祀性、民间性、娱乐性的特点,是高原民族宗教信仰观念、生活习俗、生活风格的反映,也是当地民间艺术(神话传说、民歌创作、音乐舞蹈、化妆服饰、剪纸等)的集中体现,表现了高原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有重要的文化和民俗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在历史文献中,我们还未找到有关神教的更为详细的资料,它的发展脉络和仪式,还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仅靠我们接触看到的和采访得来的材料,毕竟带有某种局限性,而且,跳神活动随着时代也处在变异中。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师公跳神的祭祀活动,则展现的是一些丰收图,民俗风情的面画。
清代康、雍间吴之挺《竹枝词》第五首写的迎神赛会的情况是:
五月清明作道场,村村迓鼓拜龙王。
巫阳抢得灵湫至,一路甘霖作麦香。
明末清初临洮诗人张晋写的《迎神曲》,显得更为详尽具体:
桃花吹风杏花雨,山口春入古庙宇。
石炉突突香烟举,吹竽撞钟纷歌舞。
巫娘婆娑唱神来,土壁龙蛇眼欲开。
纸钱绕红飞蝶灰,精灵和乐不能回。
初祝螟虫化为水,大家再祝旱魃死。
殷勤拜跪三祝己,田熟牛肥疾病止。
献神羊猪酬神酒,送神神归神保佑。
白马金袍神康寿,年年与我好麦豆。
师公跳神中,迎接水神龙王,是一个大关节,是它的主要活动。我在《临洮端午迎接八位官神赛会风俗的调查》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从略。不过官神人数各地不相统一,衙下集寺洼庙会有十二位,临潭、岷县有十八位,还多了几位女性。各地都有自己的风情特色。
综上所述,在高原这一独特环境下,孕育产生的扇鼓傩舞仪式,它历史久远,受多种宗教的影响,形式独特,具有原始性、祭祀性、民间性、娱乐性的特点,是高原民族宗教信仰观念、生活习俗、生活风格的反映,也是当地民间艺术(神话传说、民歌创作、音乐舞蹈、化妆服饰、剪纸等)的集中体现,表现了高原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有重要的文化和民俗研究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五
根据文化学的研究,很多学者把中国文化分为八大文化区,甘青为其中之一。高原地带、高山大河、深沟塬峁的自然环境,寒冷、干旱的气候条件,多民族居住、比较闭塞、长期以游牧为主(兼农耕)的社会形态,形成独特的文化系统,使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内在优势。带来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充满勃勃生机。即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的“文化核心”。当然,甘青文化的根柢是民间文化。其中包括神话传说、口头创作、音乐歌舞、赛马、民间信仰等。在民间文化土壤中,这几样东西是共生的,构成一种文化生态。作为扇鼓傩舞来说,某种程度上是民间艺术的综合体,代表了民间艺术的风貌。
诚然,它产生的根源是宗教的,以宗教信仰为目的。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一著名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页)对神教来说,自然也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往往简单地记住了马克思的结论,却忘掉了马克思的论证过程,特别是头一句。宗教除了对人民有麻醉作用外,对人确有一定的精神慰籍作用,对紧张焦虑的心理起缓解作用。从另一方面说,科学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宗教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尽管宗教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是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183)。
神教除了宗教的内容外,还有它的外在艺术形式。任何宗教为了吸引信众,增强教育感染作用,总是采取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达到宣传效果的。空洞的说教,是没有力量的。其中包括编唱的生动的神话传说故事,道场装饰,宗教音乐(声乐与器乐)、优美多姿的舞蹈等,特别是歌舞。郑玄在《诗谱》中就说过:“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由娱神向娱人方面转变,以至达到娱人为主这点上,神教比起别的宗教,似乎更为突出。在民间,观看一次隆重热烈的跳神活动,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它以色彩绚丽的各种旗帜、经幡,富有韵味的祷词演唱,特别是以节奏明快、高亢嘹亮的扇鼓击打、队形变化、矫健勇猛的舞蹈,这一富于高原特色的文艺形式吸引着感染着广大群众。歌舞,盛开在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艺术之花,是民族情绪最直接的宣泄和表达。我们从中可以受到一些启发,何不利用这种扎根群众、群众喜爱的扇鼓傩舞,加以改造、提高,“旧瓶装新酒”,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创作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歌舞,参与各种庆典活动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丰厚的民间土壤,才能长出独特的异卉奇葩!这发掘整理的工作,将是宣传文化部门及文艺工作者的全新使命!
根据文化学的研究,很多学者把中国文化分为八大文化区,甘青为其中之一。高原地带、高山大河、深沟塬峁的自然环境,寒冷、干旱的气候条件,多民族居住、比较闭塞、长期以游牧为主(兼农耕)的社会形态,形成独特的文化系统,使它较多地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内在优势。带来一种雄健豪迈、清新自然、质实贞刚的格调,充满勃勃生机。即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所称的“文化核心”。当然,甘青文化的根柢是民间文化。其中包括神话传说、口头创作、音乐歌舞、赛马、民间信仰等。在民间文化土壤中,这几样东西是共生的,构成一种文化生态。作为扇鼓傩舞来说,某种程度上是民间艺术的综合体,代表了民间艺术的风貌。
诚然,它产生的根源是宗教的,以宗教信仰为目的。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一著名的论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页)对神教来说,自然也是合适的。但是我们往往简单地记住了马克思的结论,却忘掉了马克思的论证过程,特别是头一句。宗教除了对人民有麻醉作用外,对人确有一定的精神慰籍作用,对紧张焦虑的心理起缓解作用。从另一方面说,科学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宗教解决精神生活的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尽管宗教和科学的领域本身是界限分明的,可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一个形象来比喻:科学没有宗教就象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象是瞎子”。(《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182—183)。
神教除了宗教的内容外,还有它的外在艺术形式。任何宗教为了吸引信众,增强教育感染作用,总是采取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达到宣传效果的。空洞的说教,是没有力量的。其中包括编唱的生动的神话传说故事,道场装饰,宗教音乐(声乐与器乐)、优美多姿的舞蹈等,特别是歌舞。郑玄在《诗谱》中就说过:“巫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盖在上古之世……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由娱神向娱人方面转变,以至达到娱人为主这点上,神教比起别的宗教,似乎更为突出。在民间,观看一次隆重热烈的跳神活动,无疑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它以色彩绚丽的各种旗帜、经幡,富有韵味的祷词演唱,特别是以节奏明快、高亢嘹亮的扇鼓击打、队形变化、矫健勇猛的舞蹈,这一富于高原特色的文艺形式吸引着感染着广大群众。歌舞,盛开在民族文化土壤中的艺术之花,是民族情绪最直接的宣泄和表达。我们从中可以受到一些启发,何不利用这种扎根群众、群众喜爱的扇鼓傩舞,加以改造、提高,“旧瓶装新酒”,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创作一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歌舞,参与各种庆典活动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丰厚的民间土壤,才能长出独特的异卉奇葩!这发掘整理的工作,将是宣传文化部门及文艺工作者的全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