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玄吧 关注:10,662贴子:123,722
我偷偷摸摸自床尾绕过去,那窗扉闭合,隐约透进月光来,我只看一眼,边瞬时屏住了呼吸。
只见那窗户之上,清晰的印出了个影子。那影子一动不动,可看出是个人倒挂着从外边贴在窗上,我屏息看着,手已摸上了剑鞘。
大半夜里瞧见这东西,实在是不能更醒神了。
那外头挂着的人一丝气息也无,就这样贴在窗上,仿佛一只倒挂的壁虎。我正斟酌是否该先行破窗,可这样会扰玄月安眠,忽而听见“啪嗒”一声。
水声。
于万籁俱寂之中,愈发明显。
我握住剑,突然背后掌风袭来,我下意识抽剑回身,却撞入一人怀里。那人笑道:“我道是如何,沧儿这大半夜起来,竟是要向我投怀送抱不成?”
是玄月。
我来不及回话,当即回头看那窗上的影子,却不想那影子仍牢牢贴在窗上,一动不动。
玄月也注意到那窗上的东西,便收了笑意。他凝神看了那影子片刻,忽而走上前去,我想跟上去,他却道:“沧儿,点起烛火,去喊管事儿的来。”
我咬了咬牙,方才应道:“好。”
我点起灯火下楼,找来守夜的管事。管事的一脸睡眼惺忪,却在进房后惊恐得吐不出分毫抱怨。
我站在他前边,玄月已拉开了窗户,那窗户后的人也现出真容。
其实已经不能算是人,该说是一具尸体。
尸体被倒吊在窗户外头,神色定格在死亡的那个瞬间,七窍崩血,神色僵直,喉管被破开的伤口还在徐徐滴血,顺着倒过来的面颊流下,落在窗栏上。
那股随夜风被窗户隔绝在外面的血腥味逐渐扩散开来,溢满了整个房间。
玄月回过头看着我们,淡淡道:“处理了罢。”
.
死的是这店中负责堂前茶水侍奉的小二,这客栈之中关系错综复杂,杀人者却偏偏把尸体挂在了我们窗外,目的怕是不简单。
此处位于两国交境之处,我原以为客栈老板会选择报官,却不想只是来了一行官差打扮的人,将尸体粗鲁收拾,检阅了我们的通关文牒,便直接离去了。
那老板娘送走了官差,婀娜地扭进房来,对玄月道:“小公子,奴替您打发了这些个官爷,也死了个得力的帮手。您说说,这笔帐要怎的才能结清楚?”
那手颇妖娆地伸过来,指上蔻丹色泽鲜丽。我伸手挡道:“店家,自重。”
玄月寻了个椅子坐下,道:“承了店家的情,自然会还的。”说着给自己倒了杯茶,“还请店家替我换间房,这屋中怕是住不得了。”
老板娘眉眼一挑,笑道:“那是自然。”
.
在北国已有两日,其间玄月不过带我四处游荡,逛了逛夜里的灯市,街巷里孩童带着面具提灯穿梭,整条长街灯火漫漫无所熄,听闻这是北国的年节。
玄月从街边商贩手里取了个白莹莹的面具,道:“沧儿试试,颇应景。”
我蹙眉瞅着那面具,应景是应景,就是有点傻。
忽而冷香扑鼻,眼前玄月的衣襟凑上来,他将那面具绳结在我耳后系好,我耳中轰然一响,周遭吵嚷似是都听不到,只余他略微发凉的手指拨过我头发的触感。
当真是要命啊。
幸有这面具遮掩,我面颊有些发烫,他甚至伸手理了理我的发鬓,我伸手挡了挡,道:“好了。”
玄月轻笑一声退开来,少年人的瞳仁在灯火之下熠熠生辉,仿佛整个长街的灯影都收进了他的眼睛里。他这样好看。
我低下头,斟酌是否要将玉的事情告知他。可这未免太过残忍,我如何能让他晓得,这不过是个幻境,而我总归是要出去的。人生在世,再没有什么是比被告知周遭一切都是虚妄要更加痛苦的了。
是了,再没有比幻想破灭更残忍的了。
只见那窗户之上,清晰的印出了个影子。那影子一动不动,可看出是个人倒挂着从外边贴在窗上,我屏息看着,手已摸上了剑鞘。
大半夜里瞧见这东西,实在是不能更醒神了。
那外头挂着的人一丝气息也无,就这样贴在窗上,仿佛一只倒挂的壁虎。我正斟酌是否该先行破窗,可这样会扰玄月安眠,忽而听见“啪嗒”一声。
水声。
于万籁俱寂之中,愈发明显。
我握住剑,突然背后掌风袭来,我下意识抽剑回身,却撞入一人怀里。那人笑道:“我道是如何,沧儿这大半夜起来,竟是要向我投怀送抱不成?”
是玄月。
我来不及回话,当即回头看那窗上的影子,却不想那影子仍牢牢贴在窗上,一动不动。
玄月也注意到那窗上的东西,便收了笑意。他凝神看了那影子片刻,忽而走上前去,我想跟上去,他却道:“沧儿,点起烛火,去喊管事儿的来。”
我咬了咬牙,方才应道:“好。”
我点起灯火下楼,找来守夜的管事。管事的一脸睡眼惺忪,却在进房后惊恐得吐不出分毫抱怨。
我站在他前边,玄月已拉开了窗户,那窗户后的人也现出真容。
其实已经不能算是人,该说是一具尸体。
尸体被倒吊在窗户外头,神色定格在死亡的那个瞬间,七窍崩血,神色僵直,喉管被破开的伤口还在徐徐滴血,顺着倒过来的面颊流下,落在窗栏上。
那股随夜风被窗户隔绝在外面的血腥味逐渐扩散开来,溢满了整个房间。
玄月回过头看着我们,淡淡道:“处理了罢。”
.
死的是这店中负责堂前茶水侍奉的小二,这客栈之中关系错综复杂,杀人者却偏偏把尸体挂在了我们窗外,目的怕是不简单。
此处位于两国交境之处,我原以为客栈老板会选择报官,却不想只是来了一行官差打扮的人,将尸体粗鲁收拾,检阅了我们的通关文牒,便直接离去了。
那老板娘送走了官差,婀娜地扭进房来,对玄月道:“小公子,奴替您打发了这些个官爷,也死了个得力的帮手。您说说,这笔帐要怎的才能结清楚?”
那手颇妖娆地伸过来,指上蔻丹色泽鲜丽。我伸手挡道:“店家,自重。”
玄月寻了个椅子坐下,道:“承了店家的情,自然会还的。”说着给自己倒了杯茶,“还请店家替我换间房,这屋中怕是住不得了。”
老板娘眉眼一挑,笑道:“那是自然。”
.
在北国已有两日,其间玄月不过带我四处游荡,逛了逛夜里的灯市,街巷里孩童带着面具提灯穿梭,整条长街灯火漫漫无所熄,听闻这是北国的年节。
玄月从街边商贩手里取了个白莹莹的面具,道:“沧儿试试,颇应景。”
我蹙眉瞅着那面具,应景是应景,就是有点傻。
忽而冷香扑鼻,眼前玄月的衣襟凑上来,他将那面具绳结在我耳后系好,我耳中轰然一响,周遭吵嚷似是都听不到,只余他略微发凉的手指拨过我头发的触感。
当真是要命啊。
幸有这面具遮掩,我面颊有些发烫,他甚至伸手理了理我的发鬓,我伸手挡了挡,道:“好了。”
玄月轻笑一声退开来,少年人的瞳仁在灯火之下熠熠生辉,仿佛整个长街的灯影都收进了他的眼睛里。他这样好看。
我低下头,斟酌是否要将玉的事情告知他。可这未免太过残忍,我如何能让他晓得,这不过是个幻境,而我总归是要出去的。人生在世,再没有什么是比被告知周遭一切都是虚妄要更加痛苦的了。
是了,再没有比幻想破灭更残忍的了。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吧友爆料LPL转会期战队名单1620720
- 2警方通报“王宝强被举报诈骗”1431324
- 3羊毛月北大学历被质疑造假1321152
- 4最好的高中同学离开了我1018899
- 5黑神话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提名1013142
- 6胖东来卫生巾区遭哄抢868300
- 7电影《好东西》疑似拉踩男性司机812592
- 8TE晋级亚邀四强799089
- 9吴柳芳账号被禁止关注736340
- 10刘青松自曝加入TES682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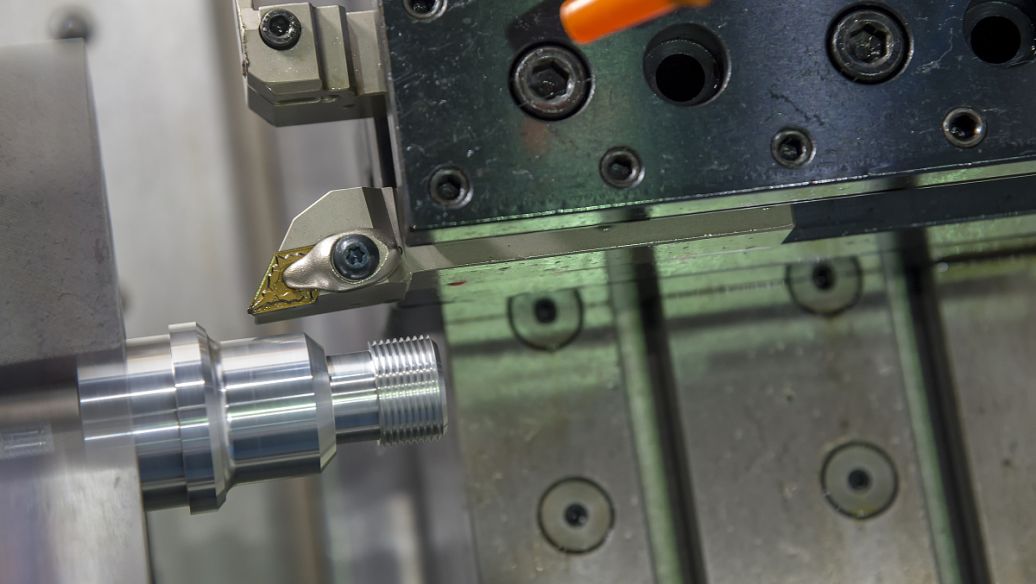





 流年似水
流年似水


